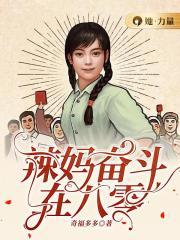笔趣阁>暴躁老太穿古代,先囤粮后逃荒 > 第九十二章 有人下毒(第1页)
第九十二章 有人下毒(第1页)
"哗啦——"
刘老太把一筐活蹦乱跳的小鱼倒进清水池,银亮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她粗粝的手掌拍在木桌上,震得铜秤叮当作响。
"排队!都给我排队!张三你挤什么挤?急着投胎啊?"
清晨的刘家院门前,二十多个村民提着鱼篓,在刘老太的骂声中乖乖排成长队。最前头的李四叔赔着笑递上鱼篓:"刘婶子,今儿个捞了八斤二两,您给瞧瞧。。。"
"少来这套!"刘老太一把抓过鱼篓,"上回你在鱼肚子里塞石头,当老娘忘了?"她麻利地过秤,铜钱叮叮当当落在李四叔手心,"八斤整,多给你半文钱,滚吧!"
刘老太的香辣小鱼酱远近闻名。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家院子前就排起了长队。村民们提着竹篓,里面装满了刚从河里捞上来的小鱼。刘老太坐在一张老榆木桌子后,面前摆着一杆铜秤,一文钱一斤,从不缺斤短两。
"张家的,三斤二两,算你三斤半的钱。"刘老太眯着那双锐利的眼睛,手指麻利地数出铜钱。
"刘婆婆,您这。。。"张老汉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
"少废话!你昨天送来的鱼里有两条大的,我看见了。"刘老太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刘金花做事,从不占人便宜!"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三年前,刘老太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孤老婆子,靠着在河边摸些小鱼小虾度日。直到她研制出了那种让人吃了就忘不了的香辣小鱼酱,先是卖给路过的货郎,后来连县城里的酒楼都派人来订购。
现在,刘老太成了刘家庄最富有的老人。她盖起了青砖大瓦房,雇了三个帮工,每天能做出上百罐小鱼酱。而村里的男人们也多了一项收入——每天早晚去刘家河捞小鱼卖给刘老太。
"一文钱一斤,一天捞个二三十斤不成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常这么说,"比种地来钱快多了。"
但并非所有人都为刘老太的成功高兴。
王凤站在自家破旧的院子里,隔着矮墙望着刘老太家门前热闹的景象,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她丈夫去年病逝,留下她和两个儿子,家道中落。曾经,她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
"娘,我去河边了。"大儿子柱子背着渔网准备出门。
"去什么去!"王凤突然尖声喝道,"给那老不死的送钱去?你看看咱们家这破房子,再看看她那大瓦房!"
柱子缩了缩脖子,不敢吭声。
"栓子呢?"王凤环顾四周,没看见小儿子。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去。。。"柱子话没说完,王凤就冷哼一声。
"准是又去给刘老婆子送鱼了!没出息的东西!"王凤咬牙切齿,"那老东西凭什么?她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凭什么过得比我们好?那河里的鱼本该是我们家的!我男人在的时候,谁敢在那河里随便捕鱼?"
柱子低着头不敢接话。他知道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性情大变,尤其是对刘老太,恨得咬牙切齿。
傍晚时分,栓子兴冲冲地跑回家,手里攥着十几个铜钱。
"娘!我今天捞了十五斤鱼,刘婆婆多给了两文钱呢!"栓子满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