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娘子,别这样! > 第605章 洛玉衡只手镇宗师七千五(第2页)
第605章 洛玉衡只手镇宗师七千五(第2页)
林素衣却不语,只是将信投入火盆。火焰腾起瞬间,她仿佛看见皇后当年温柔的笑容再度浮现,耳边响起那句轻柔叮嘱:“素衣啊,你要做个明白人。”如今她终于明白,那位女子一生困于权力牢笼,明知真相却无法言说,或许也曾无数次想揭竿而起,终究被身份与责任锁死咽喉。
“我们fighting的从来不是某个人。”她在日记中写道,“而是那种让人沉默的制度,那种把良知碾成灰烬的惯性。”
半月后,奇迹发生。
河北起义军首领率众归降,条件只有一个:请林先生派人去教孩子们识字。他们在占领的县衙门口立碑,上书:“从此以后,不准骗人。”
岭南私塾联盟正式成立“真史书院”,课程首条便是诵读《永昌实录》。
就连一向保守的吐蕃赞普也遣使来问:“可否赐一份记音匣?我国亦有被掩埋的历史。”
最令人动容的是,在洛阳废墟中,一群孤儿自发组建“拾音队”,每日搜寻战火遗留的碎片,希望能拼凑出一段完整的录音。领头的孩子不过十岁,被人问起为何如此执着,他仰头说道:“因为我没有爹娘,但我不想连历史也没有。”
林素衣得知此事,潸然泪下。她亲笔写下回信:
>“你们不是孤儿。你们是历史的孩子。”
春去秋来,三年光阴流转。
敦煌重建了新的静语塔,更高、更坚,塔身嵌入九十九块铭文砖,每一块都刻着一位为真相献身者的姓名。赎忆站虽屡遭摧毁,却如野草重生,如今已扩展至二十七座,遍及西域、漠北、西南夷地。
而林素衣本人,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人们说她隐居莫高窟某洞窟中,日夜誊抄《实录》全文;也有人说她化名游历天下,专为普通人记录口述史。只有少数人知道,她仍住在昭明馆后院的小屋里,每日清晨研墨、校稿、复核数据,一如三十年前初入师门时的模样。
某日黄昏,赵砚秋捧来最新一期《民间纪闻录》,封面赫然是江南一幅画卷:一群孩童围坐树下,听一位老先生讲述“钟声九响”的故事。画旁题诗曰:
>**一声破雾启幽冥,
>二声惊醒万民听。
>三声父老垂泪下,
>四声儿孙记姓名。
>五声官府屏息坐,
>六声宫阙起寒星。
>七声天地同悲泣,
>八声江海共潮鸣。
>九声过后山河改,
>百代犹闻钟磬声。**
林素衣读罢,轻轻抚摸青铜小钟,指尖滑过那九道凹痕。她忽然觉得,这钟声从未停止。它藏在每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唇齿之间,躲在每本被悄悄传阅的手抄本页脚之下,响在母亲哄孩子入睡时低吟的《思源谣》旋律之中。
夜深人静,她独坐灯下,提笔续写《实录》终章:
>“历史并非王者的家谱,亦非胜利者的宣言。它是千万无名者的眼泪与呐喊,是被踩进泥土仍不肯熄灭的星火。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倾听,真相就未曾死去。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能决定??
>让未来不再重复同样的谎言。”
窗外,新铸的铜铃随风轻响。
仿佛回应着什么。
又仿佛,只是在等待下一个敲钟人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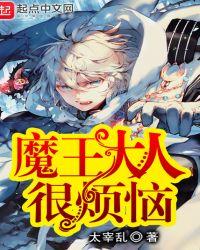

![娇气甜攻总被反派盯上[快穿]](/img/399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