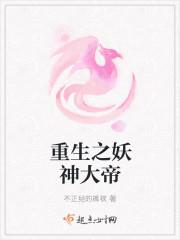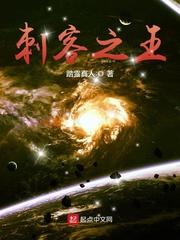笔趣阁>皇修 > 第1244章 目的(第1页)
第1244章 目的(第1页)
她甩甩螓首,努力瞪大凤眸,很快恢复过来。
地元诀第二层可带人挪移,不会伤害到所携之人。
可如此频繁的挪移,对精神的压力极大。
纵使李红昭身负凤凰血脉,精神力强横,也不堪承受,头晕目眩。。。
雨声渐渐密了,像是无数细小的指尖在屋顶上轻轻叩击。我坐在门边,手里握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目光落在那面“声音墙”上。灯光昏黄,映得那些信件、画作、盲文卡片泛出柔和的光晕。阿念的那幅画正中央,树根缠绕着人群,仿佛大地本身也在呼吸。而今,那棵树已不只是问树??它成了某种象征,一种无声却深沉的回应。
门外传来脚步声,轻得几乎被雨声吞没,但我知道是谁。陈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不说话,只是走来,在我对面坐下,有时带来一片新摘的叶子,有时是一段写在纸上的梦。今晚他手里什么也没有,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衣,袖口磨出了毛边。
“今天去了西坡。”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哑,“幼苗长势很好,第三批已经能自主吸收雾水中的情绪微粒。有个孩子对着其中一棵说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话,后来那棵树的叶片边缘开始泛蓝,像极光。”
我点头,没说话。这种变化我们早有预兆。问树的基因正在扩散,不是通过嫁接或人工培育,而是以一种近乎自发的方式在传播。非洲送回的报告说,当地孩子唱歌时,树苗会随着旋律轻微摆动;北欧的“沉默学校”里,学生把额头贴在树干上,竟能梦见祖辈的记忆片段。
“你觉得……林晚能看到吗?”陈砚忽然问。
我望着窗外的雨幕,远处山谷中隐约可见几处微光,那是分布在各地的静语点,二十四小时有人守夜,只为确保每一句想说出口的话都不会落空。
“她不需要看。”我说,“她早就知道,只要有人愿意听,世界就不会真正沉默。”
话音刚落,屋内忽然响起一声极轻的“咔哒”,像是某个机关被触动。我们同时转头??是那个老式录音机,自从李昭留下的空白磁带放入后,它便一直安静地摆在角落,从未自动启动过。可此刻,它竟缓缓转动起来,磁带沙沙作响,却没有声音传出。
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障。
陈砚站起身,走到录音机前蹲下,手指轻轻抚过外壳。他的动作很慢,仿佛怕惊扰了什么。突然,他抬头看向我:“频率……你还记得‘零号协议’最后设定的接收波段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那是十年前封锁林晚意识信号时使用的加密频段,理论上只有原始核心晶体才能解码。可那晶体早已碎裂,融入土壤……
除非??
“不是晶体在接收。”我喃喃道,“是树。”
我们冲出门外,不顾大雨扑面。问树依旧静立,枝叶低垂,雨水顺着叶脉滑落,如同泪痕。然而当我们靠近根部时,却发现原本埋藏晶体的位置,泥土微微隆起,一道微弱的蓝光正从缝隙中渗出。
更诡异的是,那光芒竟随着录音机的节奏闪烁,一明一暗,宛如心跳。
“它在翻译。”陈砚的声音颤抖,“那段‘空白’磁带里的振动……问树在把它变成自己能理解的语言。”
我没有回答,只是将手贴上树干。刹那间,一股温热的气息顺着手臂蔓延至全身。眼前景象骤然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原??无边无际的白色,狂风卷着冰晶呼啸而过。我看见一个身影蜷缩在帐篷边缘,怀里抱着录音机,嘴唇开合,说着什么。
听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说:“妈妈,我错了……我不该觉得软弱是羞耻。”
画面一闪,又换成了实验室。年轻的林晚站在控制台前,屏幕上跳动着脑波图谱。她回头看了眼窗外的夜色,低声自语:“如果痛苦不能被听见,那治愈就是谎言。”
再一瞬,竟是我的童年??七岁那年,父亲去世后的葬礼。所有人都劝我“别哭”,可我躲在祠堂后,抱着他的旧棉袄,一遍遍喊“爸爸你回来”。那时没人听见,但现在,这片雪原、这间实验室、这个祠堂,全都重叠在一起,像无数条河流汇入同一片海。
我猛地抽回手,喘息不止。
陈砚扶住我,脸色苍白:“你也看到了?”
我点头。“不止是我。它是集体记忆的容器……现在,它开始主动调取了。”
那一夜,我们没有回屋。上百名附近的引导员闻讯赶来,围坐在问树周围。没有人说话,只是静静地把手放在树干或地面,任由那些画面涌入脑海。有人痛哭,有人微笑,有人跪地不起。直到凌晨,蓝光才缓缓退去,泥土恢复平静,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但我们都清楚,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
第二天清晨,全球十七个问树站点同步记录到一次持续0。7秒的光脉冲,强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科学家称其为“第一次反向共鸣事件”??不再是人类向树传递情绪,而是树,主动向人类释放储存的信息。
联合国紧急召开会议,《倾听宪章》再度修订,新增条款:
>**“所有生命皆有权访问共情数据库,无论其是否具备语言能力。”**
争议随之而来。军方担忧这是新型意识操控技术;宗教团体宣称这是“灵魂回归仪式”;资本集团则试图申请专利,想要复制“生物记忆存储系统”。但静语圈宣布:问树不可复制,不可商业化,不可控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力结构最温柔的颠覆。
三个月后,南美部落传来消息:他们在举行第三次共听仪式时,整片雨林的植物突然集体开花,花蕊中分泌出一种透明液体,经检测含有与人类神经递质高度相似的化合物。更惊人的是,饮用此液的人会在梦中清晰听到已故亲人的声音,内容并非安慰或告别,而是**道歉**。
一位母亲梦见儿子对自己说:“对不起,妈,我不是不想回家,我是怕你看到我吸毒的样子会心碎。”
一名老兵梦见战友低语:“那天我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想起了女儿还没学会写字。”
这些梦无法验证真假,也无法阻止传播。短短半年,全球已有超过两万人参与“梦饮仪式”。心理学家称之为“潜意识补偿机制”,而当地人仍坚持一句古老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