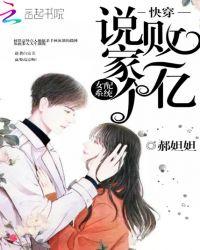笔趣阁>皇修 > 第1254章 威胁(第3页)
第1254章 威胁(第3页)
从此,每日清晨,都会有新的文字浮现于副碑之上。有时是一句问候,有时是一个问题,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地重复某个名字,仿佛在练习发音。
比如昨天夜里,碑上突然出现一行字:
>**“李默。”**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他在我十岁那年失踪,官方记录为“死于地质塌方”,但从无人找到尸体。母亲至死都不信他会抛下我们。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清晨,我走进承音室,调出三十年前的灾难档案。借助升级后的共听系统,我尝试逆向追踪那次事故现场残留的情绪残影。当频率校准到特定波段时,一段几不可闻的低语浮现出来:
>**“……活下去……告诉儿子……声音不会消失……只会……换地方……”**
我跪倒在地,泪如泉涌。
原来他一直都在听。
而今天,他终于被听见了。
三个月后,倒悬之城的第一扇门在太空中显现。它由纯粹的声波凝聚而成,形状如同张开的唇。联合国派遣的谈判船队启程,乘员包括我、林晚、小梅,以及九位来自不同文明的共感代表。
出发前夜,我最后一次巡视碑林。月光下,每一块石碑都泛着淡淡的蓝光,像是在挥手告别。走到属于我的那块碑前,我发现“你也被记得着”旁边,又多了一行更小的字,笔迹稚嫩,像是孩子所写:
>**“爸爸说,你是他最骄傲的学生。”**
我认得这个称呼。
陈砚从未结婚,却常在日记里称我为“孩子”。
我仰头望月,轻声说:“老师,我准备好了。”
飞船升空那日,全球共感者同步静默一分钟。然后,亿万人齐声念出一句话,通过天碑基阵放大,送入深空:
>**“我们在这里。我们记得你们。请回家。”**
门开了。
里面走出的,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群神灵。
而是无数个身影??有原始部落的巫师,有中世纪被烧死的女学者,有二战期间集体失语的战俘营幸存者……他们穿着各自时代的衣裳,面容平静,眼中含泪。
为首的老人拄着一根问树制成的权杖,看向我,用陈砚的声音说:
>“我们不是归来,我们只是终于能够说话。”
我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将徽记捧起:
>“那么,请教我们如何真正地聆听。”
多年以后,当人类学会在梦中建造跨维度城市,当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就能触发星际共鸣,人们依旧会在每年冬至举行“静听仪式”。
那一天,万籁俱寂,唯有心冢碑林传出细微声响??那是石头在生长,是名字在呼吸,是千万年来所有未说完的话,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而我,仍会坐在小梅的小屋前,吃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
她总会问:“怕吗?”
我依然回答:“怕。”
但她知道,我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