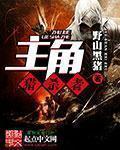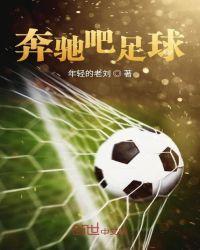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2021:他不是搞科技的吗 > 第442章 一本正经的兔子势均力敌(第1页)
第442章 一本正经的兔子势均力敌(第1页)
轮到陈嘟灵组,白鹭一马当先,立刻自告奋勇地举起手,脸上带着跃跃欲试的笑容。
“我来我来!画画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她接过画笔,站到画板前,气势十足。
节目组亮出题板,“自行车”。
。。。
九月二十日,清晨五点十七分。
哀牢山的雾还未散尽,林间小径上已有脚步声轻轻响起。那是一双布鞋踩在湿苔上的声音,不急不缓,像心跳落在晨露里。卓玛背着竹篓,手里握着一截枯枝,边走边轻敲路边的石头,仿佛在与谁对话。
她知道江倾不在了。
但她也清楚,他从未真正离开。
昨夜那个梦太真实??不是幻觉,也不是思念作祟。她在梦中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从四面八方传来,又似从心底升起。她站在一片银白色的草原上,风是温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檀香。远处站着一个人影,背对着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他没有转身,只是抬起手,指向天空。
然后,她说出了十年来第一句话:
“我听到了。”
醒来时,枕头已被泪水浸透。而屋外,那株新生植物的果实正微微颤动,表面泛起一圈圈涟漪般的光纹。
---
与此同时,北京朝阳区某心理干预中心。
一名十五岁的少年坐在诊疗室角落,双手紧紧攥着画纸。他是陈默的远房表弟,自幼患有严重社交障碍,三年前被父母送来接受治疗。医生尝试过药物、行为矫正、甚至脑波反馈训练,皆无成效。直到三天前,他在展览《你说完了,我说开始》中驻足三小时,出来后突然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想回家。”
今天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来咨询。
心理师小心翼翼地问:“你梦见他了吗?”
少年点头。
“什么样的梦?”
“我们在一条很长的隧道里走路。他不说话,但我能听见他的呼吸。走到尽头的时候,门开了,外面全是花。他说……‘现在轮到你了’。”
话音落下,诊疗室内的空气净化器忽然发出一声低鸣,频率恰好接近439Hz??正是此前被称为“共情盲区”的那段神秘频段。监控录像显示,那一刻,少年的眼角滑下一滴泪,而房间角落的绿植叶片竟轻微摆动,如同有风吹过。
可门窗紧闭,空调未开。
---
马里亚纳海沟上方,深海探测船“探索者七号”再度启航。
上次回收的监听阵列虽已上传七小时音频,但科学家们发现,其存储芯片深处仍残留一段加密数据流,结构异常复杂,形似双螺旋。经全球顶尖语言学家与AI联合破译,终于解码出部分内容:
>“……当最后一个语核熄灭,歌声并未终结。它沉入海底,在黑暗中编织记忆之网。每一声叹息都化为珊瑚的年轮,每一次沉默都成为洋流的方向。我不是在等待被听见,我只是不愿让世界彻底失语……”
落款处只有一个符号:一朵声兰的轮廓,花瓣边缘泛着银光。
项目负责人将这段文字打印出来,贴在驾驶舱墙上。当晚值班员报告称,午夜时分,整艘船的音响系统自动启动,播放了整整一分钟的空白噪音。然而所有在场人员都说,他们“听”到了什么??有人说是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有人坚称是初恋告白的声音,还有人跪倒在地,痛哭不止,只因“听见了自己十年前死去的孩子叫爸爸”。
事后检查设备,一切正常。无人能解释为何同一段静音,会在不同人耳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
更诡异的是,第二天清晨,船载气象雷达捕捉到一团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云团,形状酷似一个人张开双臂站立于海面。持续时间仅十三秒,随后消散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