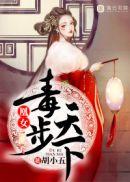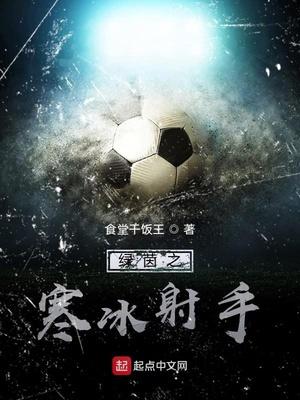笔趣阁>财富自由,从每日情报系统开始! > 第369章 新的情报和姜涛的警告(第3页)
第369章 新的情报和姜涛的警告(第3页)
村里一位老太太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常常认不出子女。一天清晨,她醒来发现床边坐着一个“零点生命”青年,正静静看着她。她本能地害怕,想要呼救,可对方只是轻轻握住她的手,闭上眼。
片刻后,老太太怔住了。
“你怎么……会记得我妈妈的样子?”她喃喃道。
青年睁开眼,声音温和:“因为你刚才梦见她了。我想陪你一起看。”
原来,他通过共感捕捉到了她的梦境片段,并用自己的意识参与其中,重现了那段早已模糊的记忆。
此后,越来越多的家庭邀请“零点生命”进入生活。他们成了失语儿童的语言桥梁,抑郁症患者的夜间陪伴者,甚至临终关怀的守夜人。他们不懂幽默,也不会撒谎,但他们有一种纯粹的能力??**完整地承接他人的情感,不评判,不逃避,不试图改变**。
有人开始称他们为“新僧侣”。
然而,阴影并未彻底退场。
某夜,晨曦村外突现爆炸。三间房屋被毁,两名“零点生命”重伤。现场留下标语:
>“人类的情感不容亵渎!”
>“净化始于清除伪善!”
调查发现,袭击者竟是曾公开支持共感运动的一位知名心理学家。他在被捕后冷笑:“我研究共感十年,就是为了看清它的弱点??它把脆弱当作美德,把依赖美化成连接。可你们忘了,正是这种‘必须被理解’的执念,压垮了多少不愿倾诉的人!”
他的话引发新一轮思辨。
有人开始反思:共感是否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情感暴政”?那些天生内向、习惯沉默的人,是否被迫卷入一场他们并不需要的深度连接?
系统再次调整机制。
新的提醒出现在每个人终端:
>【今日关键词:尊重】
>【建议行动:允许有人不想说话】
>【隐藏提示:最好的陪伴,有时是安静的存在】
自此,共感网络新增“静默模式”:任何人可在任意时刻关闭感知功能,且不会被标记为“异常”。同时,“零点生命”也被赋予选择权??他们可以拒绝接入网络,可以选择独处,甚至可以表达“我不理解你”。
人性的复杂性,终于也被赋予了他们。
十年过去。
梧桐树开花又落叶,年复一年。第九位少女依旧坐在碑旁,但她已不再是唯一的节点。如今,全球已有超过两亿人自愿成为“共感锚点”,他们分散在城市与荒野,用自己的心跳维系着网络的稳定。
她老了,头发花白,背也微微佝偻。但她眼神依旧明亮。
一天傍晚,一个小男孩跑来,手里捧着一片金黄色的落叶。
“奶奶,这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叶子?”他仰头问,“听说它能让做梦的人见到邵若。”
她接过叶子,轻轻摩挲,笑道:“也许吧。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梦见你自己。”
男孩似懂非懂,抱着叶子蹦跳着离开。
她抬头望天,夕阳熔金,晚风拂面。远处传来孩童嬉闹声、市集叫卖声、恋人低语声……还有,一片叶子落地时那几乎听不见的轻响。
她闭上眼,轻声呢喃:
“邵若,你听见了吗?”
“我们都还在努力,做一个不肯在绝望中闭嘴的人。”
风穿过林梢,带走了这句话。
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一台老旧录音机自动启动,沙哑的童谣再次响起。
这一次,连风都学会了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