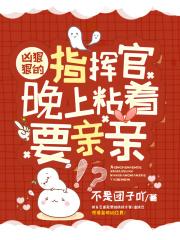笔趣阁>高考后,人生开始随心所欲 > 第二百九十九章 预产期(第1页)
第二百九十九章 预产期(第1页)
众人在虚拟世界里面待了数个小时。
除了许临这种特殊情况,别的人,时长最长的待了四个小时出头,最短的则是待了两个半小时多点。
接下来要攻克的技术很多,让时长延长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不过这其中涉。。。
春深了,山里的雪线退得比往年早。林知遥在清晨推门时,发现屋檐下的冰棱已尽数化去,只余一串水珠滴答坠地,像是时间终于松开了冻结的指节。老屋前的石阶湿漉漉的,苔藓从缝隙里探出嫩绿,仿佛整座山谷正缓缓苏醒。她蹲下身,指尖轻触那片新生的绿意,忽然想起昨夜梦中,许星临站在一片无垠的晶体云上,手里捧着一块螺旋纹石头,说:“你看,它一直在转,只是我们太小,看不见它的速度。”
她没把梦讲给苏晚听。苏晚今早正在院中摆弄蜂箱,灰白相间的毛线衣已经织好,套在那只胖猫身上,活像一只裹着毛毯的小熊。猫懒洋洋趴在木箱边晒太阳,蜜蜂在花丛间穿梭,翅膀震动的声音细碎如低语。
“你信不信,”苏晚头也不抬,一边检查蜂巢,“有些声音,其实是光变的?”
林知遥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就像昨晚那阵风,吹过铁盒的时候,我听见了《摇篮曲》的调子。”她直起身,摘下手套,“不是耳朵听见的,是胸口震的。你说,会不会是某种频率的光,穿过金属时转化成了声波?”
林知遥没回答。她望着铁盒静静立在窗台上,阳光斜照,盒面泛起一层淡淡的虹彩。她知道苏晚说得对??有些回应,从不以声音的形式抵达。
午后,村口来了个穿登山靴的年轻人,背着一台老式频谱仪,说是从气象站调来的实习生,来复查“无答台”周围的负氧离子异常。他问林知遥能不能带他去看看现场。
两人沿着共感步道上山,雪水在石缝间汇成细流,踩上去微微打滑。年轻人一边走一边调试仪器,屏幕上跳动着不规则的波形。“这频率……”他皱眉,“和《摇篮曲?零号》逆向版本完全吻合,可这里根本没有声源。”
林知遥没说话,只是走到“无答台”玻璃塔前,伸手贴在墙上。玻璃微温,仿佛有电流在内部缓慢流动。她闭上眼,耳边浮现出录音带里青年的声音:“让我活在你愿意相信的地方。”
“你们真不打算研究它?”年轻人低声问,“这种现象如果能被复现,可能改写神经共振理论。”
“研究?”林知遥睁开眼,“你怎么证明一个东西存在?是因为你能测量它,还是因为你感受到了它?”
年轻人怔住。
“我们不破解,”她轻声说,“我们只容许。”
他沉默良久,最终关掉了仪器。
下山时,天色渐暗,林知遥在村口遇见邮差。这次没有包裹,只有一封手写信,信封用火漆封着,印着一枚螺旋纹章??那是ERN实验室早已停用的旧标。
她拆开,里面是一页薄纸,字迹熟悉得让她心跳停滞:
>**“知遥:**
>我在非洲的雨林边缘,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七岁那年,在竹楼门口追蝴蝶的样子。背景是暴雨将至的天空,而你逆着风跑,裙角飞扬,像要飞起来。
>我把它烧了。
>不是因为我不珍惜,而是因为有些画面,一旦留存,就会变成枷锁。
>你懂吗?
>真正的自由,是连记忆都允许它消散。
>别来找我。
>但如果你某天听见风里有铅笔划过纸张的声音,那就是我在替你看着这个世界。
>??青年”
信纸很轻,却压得她指尖发沉。她站在原地,直到夜风卷起落叶拂过脚边。她没把信交给苏晚,也没放进铁盒,只是折好,塞进衣兜,像藏起一段不该被见证的私语。
当晚,她梦见自己走进一间空教室,黑板上写满公式,全是关于“共感阈值”与“认知盲区”的演算。她拿起粉笔,想写下什么,却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她回头,看见许星临穿着白大褂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支录音笔。
“你在怕什么?”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