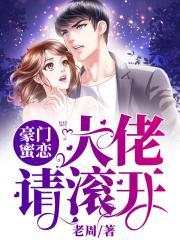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36章 谁家摄影师会把军舰拍成模型小渔船(第3页)
第636章 谁家摄影师会把军舰拍成模型小渔船(第3页)
“也许,疯的不是他们,是我们。”
半年后,秋天。
中国西北某戈壁试验场,军方进行新型通信干扰测试。导弹升空前,控制系统突遭未知信号入侵,导航界面竟跳出一行古汉字:
“莫忘初心,常忆灯火。”
事后调查发现,该信号源自一枚上世纪六十年代退役的短波电台残骸,早已掩埋地下十余米,理论上不可能工作。更诡异的是,那段文字的编码方式,竟与敦煌出土唐代《金刚经》刻本完全一致。
而在民间,“声音避难所”已发展至三千余处,覆盖六大洲。它们形态各异:有藏在地下室的秘密诗社,有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太阳能帆船学校,有由废弃电话亭改造的“独白亭”,甚至还有专为盲人设立的“触觉音乐会”,通过振动频率传递旋律。
人们不再追问“这样做有用吗”,而是渐渐明白:
**意义不在结果,而在选择本身。**
林浩然依旧奔波各地,不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传歌人”。他不再试图掌控全局,也不再担忧失败。他知道,真正的胜利不是击败敌人,而是让更多人相信??
你可以哭,可以迷茫,可以说错话,可以唱跑调,依然值得被爱。
某个雨夜,他在乌镇老唱片茶馆遇见一位九十岁的退休语文教师。老人颤巍巍地从箱底取出一卷手抄歌本,泛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地民谣,最后一行写着:
>“若后人问起这个时代,
>请告诉他们:
>我们曾用歌声,
>抵挡过钢铁与代码的寒冬。”
林浩然一页页翻看,指尖微微发抖。
临走时,他买下一枚老式蜡筒留声机,准备带回给阿吉拉姆。
归途中,暴雨倾盆。山路泥泞,车辆抛锚。他只好徒步前行,背着沉重的机器,在雷鸣电闪中跋涉。雨水顺着额头流下,模糊了视线。
忽然,前方黑暗中亮起一点微光。
接着是第二点,第三点……
十几个村民打着伞走来,每人手中提着一盏纸灯笼。
为首的汉子笑着说:“听说你在送一台会唱歌的老机器?咱们怕它淋坏了,特意来接。”
林浩然说不出话,只觉胸口滚烫。
众人护送他至村口,临别时,那位汉子塞给他一张湿漉漉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首新编的顺口溜:
>“电子心冷铁做肠,
>不懂娃儿想亲娘。
>好歌不在云端藏,
>半句乡音暖肝肠。”
他收好纸条,抬头望天。
乌云裂开一道缝隙,月光洒落如银。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
这场战争从未结束,也不会结束。
但它已经赢了。
因为在无数个平凡的夜晚,
总有人在无人处轻轻开口??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只是为了,
不让世界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