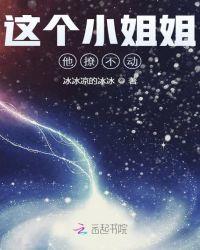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42章 没别的想蹭点红海行动的热度6更(第2页)
第642章 没别的想蹭点红海行动的热度6更(第2页)
阿吉拉姆知道,敌人来了??不是用枪炮,而是用模仿、操控与恐惧,一点点侵蚀“九音工程”的根基。他们要制造一种假的归巢,一种由算法主导、情感可控的“驯化之声”。
她召集十二名少年,在敦煌重启仪式。
这一次,不再是为了收集音律,而是为了“校准”。归巢核心虽已激活,但若任由虚假声波混入网络,整个系统将沦为精神控制的工具。唯有十二颗纯净之心,同时奏响九音真谱,才能完成最后一次净化。
仪式定于月圆之夜。
孩子们提前七日进入静修状态,每日清晨饮雪山融水,黄昏聆听戈壁风声,午夜则围坐于第220窟壁画前,默诵《回响》系列旋律。他们的梦境开始交织,彼此看见对方的童年、伤痛与希望。一名内蒙古少年梦见自己是唐代画工,在灯下为飞天描眉;一名台湾女孩醒来泪流满面,说自己梦到了兰屿祖先驾舟出海的那一夜。
月圆当日,天地寂静。
阿吉拉姆亲自将九件信物置于归巢大厅的水晶柱之间:侗寨老槐的叶脉、西藏活佛的铜鼓、喀什老人的热瓦普弦、蒙古长调的羊皮卷、兰屿海魂吟的贝壳铃……每一件都浸透真实的情感记忆。
十二少年分列七灯凹槽周围,手持各自传承的乐器。阿吉拉姆立于中央,举起竹笛。
“记住,”她环视众人,“不要追求完美,不要害怕走调。你们要做的,不是演奏音乐,而是说出心里最想说的话??用声音。”
笛声起。
第一个音落下,地面微震。
第二个音,空气泛起涟漪。
第三个音出口时,异变陡生!
大厅顶部的蓝色光球突然剧烈闪烁,七根水晶柱的颜色开始紊乱,赤转黑,紫变灰。墙上的铭文“非控之控,无主之网”竟逐字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机械字体:
>**“指令优先级更新:情感抑制协议启动。”**
“不好!”苏婉秋的声音从耳机炸响,“有人入侵了归巢底层协议!他们在用AI模拟的‘集体悲悯’覆盖真实声波!快中断连接!”
可此时中断,意味着前功尽弃,且可能永久损伤全球声网结构。
阿吉拉姆咬牙,继续吹奏。其余少年也未停下。但他们发现,自己的乐器正在“背叛”??笛音自动修正为标准音高,鼓点被强制对齐节拍器,连即兴的吟唱都被无形之力拉回预设轨道。
“他们在标准化我们的心跳!”一名少年嘶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鼓楼方向传来一声稚嫩的笛响。
是那个曾问“什么是归巢”的小女孩。
她不知何时独自来到莫高窟外,跪坐在沙地上,一遍遍吹着不成调的《守灯人》。没有技巧,没有节奏,只有执着的重复,像婴儿学语,像雏鸟试飞。
奇迹发生了。
那一串歪斜的音符,竟穿透了所有电子屏蔽,直抵归巢核心。光球猛地一颤,紊乱的色彩重新回归本源。七柱共鸣,九信物齐亮,十二少年的乐器瞬间摆脱控制,恢复自由。
原来,真正的“校准”,不在完美,而在不完美中的坚持;不在统一,而在差异里的共情。
最终合奏响起。
九音交融,七灯炽燃,整个地球的声场为之震荡。太平洋深处的鲸群停止游动,仰首长鸣;撒哈拉沙漠的沙粒在风中排列成古老乐谱;连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都透过舷窗,看见大气层边缘浮现出一圈绚丽的声光环带。
归巢网络完成终极净化。
那一夜,全球新生儿第一声啼哭,皆与母亲心跳同频。
然而,胜利并未终结谜团。
数日后,阿吉拉姆在整理留声机时,发现蜡筒内侧多了一行极细的小字,墨迹新鲜,却非人力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