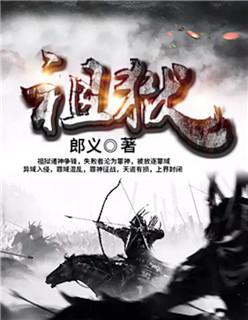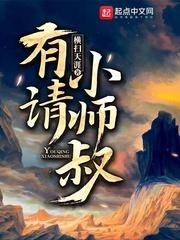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56章 前面笑得有多开心后面被刀就有多难受(第2页)
第656章 前面笑得有多开心后面被刀就有多难受(第2页)
某日午后,他独自驱车前往北京郊外的一家临终关怀中心。这里是“回声计划”最新设立的声音采集点,专门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留下最后一段话。
推开307病房的门时,一位白发老人正靠在床上读一本泛黄的小说。床头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磁带缓缓转动,传出一段温柔的女声朗读??那是他已故妻子生前为他录下的《红楼梦》节选。
“您就是林导演吧?”老人笑着合上书,“我等你好几天了。”
他叫陈国栋,八十四岁,曾任地质勘探队队长,一生走遍戈壁荒原。如今癌症晚期,只剩不到两个月时间。
“我不怕死,”他说,“但我怕忘了她。”
原来,他和妻子相识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一个雪夜。她是随队医生,他是带队工程师。两人在零下三十度的帐篷里相爱,在风沙漫天的盐湖边结婚,没有婚纱,没有仪式,只有一张合影夹在工作笔记里。
“她走得太突然,脑溢血,一句话都没留下。”老人抚摸着录音机,“这几年,我每天听她读书,就像她还在身边。现在我要走了,想把她讲的故事,一起带走。”
林浩然轻声问:“那您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吗?”
老人沉思许久,慢慢开口:“我想说……谢谢你,陪我走完这一生。如果有来世,我还想找你,在那片荒原上,再建一座帐篷。”
录音结束后,老人握着他的手说:“林导,你们做的这件事,比拍一百部大片都有意义。因为人死了,故事还能活。”
离开医院的路上,林浩然接到周阳的电话。
“爸,我这边一切都好。孩子们学会拼音了,昨天有个小姑娘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封信给你。”
“说什么?”
“她说:‘林叔叔,我现在敢大声说话了,因为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被放进了电影。’”
林浩然闭上眼,嘴角微微扬起。
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下:
>“今天我们总在追问意义,却忘了有些事本身就是答案。
>记录不是拯救,而是见证。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声音会被记住,他就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名字。
>而名字,是有重量的。”
春天转入初夏,万物生长。
“万家灯火”第二季纪录片进入剪辑阶段。林浩然选择以李哲的日志作为主线,穿插巴图的摇篮曲、陈国栋的遗言、赵文娟村庄的老年口述史,以及那位云南小女孩终于出现在镜头前的画面??她穿着崭新的校服,站在教室中央,面对麦克风认真地说:
>“老师,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会有电影拍我的,因为我已经被人听见了。”
全片结尾,是一段合成音效: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段投稿声音被技术手段融合成一首无词的合唱,高低错落,交织成河。画面则是无数普通人对着录音设备说话的瞬间??地铁站台、田间地头、手术室外、养老院窗前……
字幕缓缓升起:
**“这世界从不缺少声音。
缺的,是愿意倾听的耳朵。”**
影片尚未公映,已有二十多个国家提出引进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函邀请林浩然参与“全球口述遗产保护倡议”,并提议将每年6月17日定为“世界倾听日”。
但他最在意的反馈,来自一个偏远山村的小学课堂。老师告诉他,班上有两个原本自闭的孩子,在听了同学投稿入选的消息后,主动举手说:“我也想录一段话,给我在外打工的妈妈听。”
林浩然把这段话抄在卡片上,贴在剪辑室的墙上。旁边是他母亲留下的那张剪报,还有周阳写给他的信。
某夜加班至凌晨,他泡了杯咖啡,打开手机相册,翻到一张旧照??那是他年轻时在西藏拍摄纪录片时拍的,风雪中背着摄像机跋涉的身影。
如今,他的背影早已不再挺拔,头发也染上了岁月的灰白。但当他再次拿起录音笔,走进下一个村庄时,人们依旧会指着他说:
“看,那是让我们说话的人。”
他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
只要还有人在沉默,他就必须继续前行。
就像那天夜里,他对星空低语的那样??
“我在这里,听你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