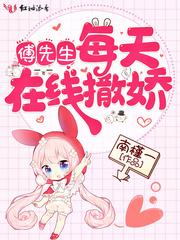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64章赛博妲己开始发力化缘神功已成(第2页)
第664章赛博妲己开始发力化缘神功已成(第2页)
教室里有人抽泣。阿?低头抹泪。
“所以你们不是在学一门技术,”林浩然环视众人,“你们是在接住那些即将坠落的声音。每一个字,都是祖先递给你们的手。”
课程持续一个月。结业仪式上,学员们集体朗诵新编《苗语归来辞》,其中一句反复响起:
>“我不怕走远,只怕忘了怎么回头。”
回到北京后,林浩然接到教育部通知: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建议,在地方课程中增设“母语启蒙”单元,内容由“语言方舟”团队提供支持。这意味着,未来每一名中国孩子都有机会在学校听到至少一段本地区少数民族或方言原声。
消息传出当晚,微博再度沸腾。“#我想让孩子听见外婆的歌#”登上热搜榜首。一位江苏网友留言:“我妈一辈子没说过几句普通话,今天她知道她的吴语童谣要进课本了,坐在沙发上哭了半小时。”
林浩然读完这条评论,起身走到M-07柜前,取出一张未标注标签的存储卡。这是最近收到的一批民间上传资料中最特殊的一份:来自浙江丽水山区,录音人是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教师,他在记忆彻底消散前,用三天时间背诵了整部《处州鼓词?忠烈传》。
技术人员分析发现,其中有十二处唱段从未见于任何文献记录。
“有些记忆会遗忘主人,但不会忘记自己。”林浩然在项目日志中写道,“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给它们一个回家的名字。”
夏天到来时,他再次启程前往新疆伊犁。其其格来信说,科尔沁草原的牧民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百人说书大会”,所有人轮流讲述巴特尔老人留下的故事片段,连续七昼夜不熄篝火。
他也受邀参加。
抵达那天,草原碧绿如海,白云低垂。远远望去,数百顶蒙古包围成圆阵,中央高台上竖立着一块巨幅投影幕布,正循环播放修复后的《成吉思汗东征记》音频波形图,宛如一道流动的星河。
其其格迎上来,怀里抱着那把牛皮琴:“林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夜幕降临,说书开始。第一位登场的是个十岁男孩,操着还不熟练的蒙古语,磕磕巴巴地讲起“铁木真少年失马”的段落。台下无人嘲笑,反而齐声鼓掌。接着是妇女、老人、退伍军人、小学教师……每个人讲一小节,有的流畅,有的哽咽,有的甚至只能念几句台词。
轮到其其格时,她抱着琴走上台,轻轻拨动琴弦。
没有说话,只有音乐响起。
那一瞬间,全场落针可闻。琴声苍凉辽远,仿佛穿越沙场烽烟,直抵人心最柔软处。林浩然闭上眼,竟在旋律中听出了《成吉思汗东征记》的主旋律变奏??那是巴特尔老人独有的起调方式,几十年未曾改变。
曲毕,其其格轻声说:“这是我爷爷教我的第一首曲子。他说,只要琴还在响,故事就不会死。”
人群爆发出长久的欢呼。
林浩然站在台下,久久不能言语。他知道,这场大会的意义早已超越纪念本身。它昭示着一种新的可能:当一代人的声音逝去,下一代不仅能继承,还能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
返京途中,他写下一封信,寄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
>“尊敬的各位同仁:
>我们常以为文化的消亡始于无人讲述。
>但我逐渐明白,真正的终结,是当人们认为‘不值得讲’的时候。
>而今,在中国的许多角落,这种‘值得’正在被重新定义。
>一位牧人因自己的歌声被认可而落泪;
>一个孩子因学会祖辈的语言而挺直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