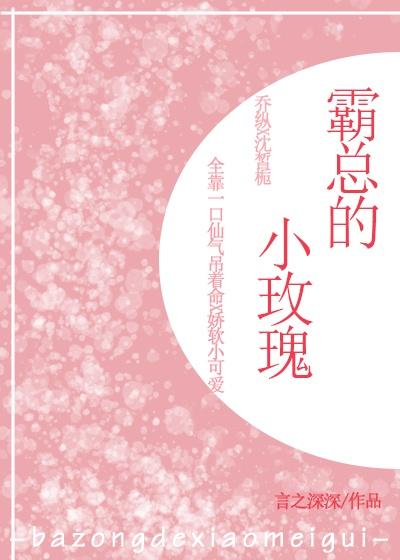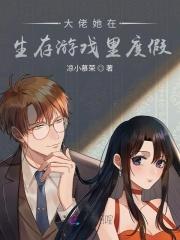笔趣阁>得罪资本后,我的歌越唱越红 > 第三百章 歌词联动 登上世界舞台一身中国范儿唱着东方情怀(第2页)
第三百章 歌词联动 登上世界舞台一身中国范儿唱着东方情怀(第2页)
上线首周,“共忆场”便收到数万条反馈。一位新疆退伍军人留言:“我在边境巡逻十年,从未听过木卡姆。可昨晚我梦见牺牲的战友,醒来打开‘共忆场’,听到一段维吾尔语挽歌,居然止住了眼泪。”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某短视频平台迅速推出挑战赛#格萨尔蹦迪版#,将扎西才让的吟唱剪辑进电子混音曲目,配以舞厅灯光与网红扭胯动作。更有营销号宣称:“这才是真正的国潮电音!”
与此同时,一家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发布新品广告,背景音赫然是“霍岭大战”中格萨尔出征的号角式唱腔,画面却是白领在写字楼里端着咖啡杯微笑打卡。文案写着:“唤醒你内心的英雄。”
沈铭恩依旧未公开回应。
直到第十天深夜,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长达十二分钟的纯音频,标题仅有一行字:**《请先学会听》**。
音频开头是三十秒绝对静默。随后,极轻微的呼吸声响起,接着是一句缓慢的藏语吟诵:“……越过十三重雪山,只为带回一具冰冷的躯体……”
紧接着,声音骤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医院监护仪的滴答声、氧气面罩的嘶鸣、老人剧烈咳嗽后的喘息……然后才是完整的“阿克琼”段落,由沈铭恩用生涩却虔诚的安多方言逐字复述。
最后三分钟,没有任何人声。只有风吹过经幡的声音,夹杂着远处一头牦牛的低鸣。
评论区长时间陷入沉默。两个小时后,第一条留言出现:“我刚才关掉所有灯,听完一遍,哭了。”
第二天,“共忆场”新增用户突破五十万。多家医院主动联系,希望将该系统用于创伤后心理干预。一位精神科医生写道:“我们试过药物、谈话疗法、艺术治疗……但从没见过哪种方式能让PTSD患者在初次接触时就产生如此强烈的归属感。”
沈铭恩却在此时做出决定:暂停一切商业合作洽谈,关闭“声脉系统”的融资通道。他在内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开始考虑估值,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背叛了第一个在火塘边唱歌给孙子听的老人。”
冬季尾声,他接到云南巍山县政府来电:一位九十岁的彝族毕摩(祭司)愿交出珍藏半生的《海菜腔?迁徙卷》手稿,条件只有一个??“必须由你亲自来取,并且当场唱给我听。”
山路崎岖,暴雨倾盆。当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那座百年老宅前时,老人正坐在檐下剥玉米。见到他,也不言语,只递过一本用油纸层层包裹的册子。
沈铭恩翻开第一页,泪水瞬间涌出。
那不是文字,而是一幅幅炭笔画:一群赤脚男女背着竹篓渡河,孩子在母亲背上熟睡,老人拄杖望天……每一幅下方都标注着对应的旋律符号与气息标记。
“这是我爷爷画的。”老人终于开口,“他们那一代人不识字,就把歌画成了路。”
当晚,沈铭恩在堂屋中央盘膝而坐,依照图画提示,尝试复现那段失传已久的“渡江谣”。起初屡屡卡顿,音准失控。直到他放下本子,闭眼回想自己徒步穿越怒江峡谷时的感受??脚下碎石滑动,耳边江涛轰鸣,背包沉重如负罪……
当他再次开口,声音竟自然贴合了画中人物的步伐节奏。
老人听着听着,忽然起身,从柜底取出一支用芦苇制成的古老哨笛,轻轻吹响一个引子音。沈铭恩立刻接上,两人一唱一和,宛如千年前那支迁徙队伍仍在月下前行。
黎明时分,老人握住他的手:“现在,它是你的了。”
归途中,沈铭恩收到林小满消息:“‘蝉歌’医疗授权已签,首批耳机将在三家三甲医院试点使用。我们加了那条附加条款:每位使用者首次播放前,必须聆听原唱者生平录音。”
他回复:“好。记得告诉他们,那个唱‘蝉歌’的老太太,叫杨素芬,生于1932年,卒于2018年。她一生住在江南小镇,每天清晨为病卧丈夫唱这支曲子,持续了四十六年。”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那一刻,窗外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照进车厢,落在他颈间的吟者之链上。铜铃轻颤,无声而清晰。
他知道,有些声音永远不会消失。
它们只是等待下一个愿意跪下来倾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