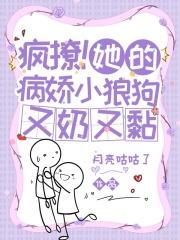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08:从山寨机开始崛起 > 第六百六十四章 智云工程师很忙(第2页)
第六百六十四章 智云工程师很忙(第2页)
“不行。”他最终开口,“我们可以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可以推送亲子沟通建议,甚至可以设计家庭共听故事模块,但绝不能让父母直接读取孩子的私密倾诉。信任一旦破裂,就再也无法重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要做的,不是打通所有壁垒,而是帮助他们在安全的前提下,自己打开门。”
会议结束后,他独自留在办公室,调出最近一周的高危预警案例。其中一个引起了他的注意:
ID:Chengdu_Teen_0415
年龄预估:14岁
所在地:成都某重点中学
关键词频现:“考砸了”“废物”“他们都会嫌弃我”
最后一次交互时间:凌晨1:23
语音内容(经脱敏处理):“我已经删了三次遗书草稿……可每次删完,又觉得更累一点。”
系统已触发三级警报,并尝试联系预留监护人电话,但无人接听。按照流程,区域合作的心理志愿者将在24小时内上门探访。
林远舟盯着屏幕,心跳加快。他忽然起身,拨通行政助理电话:“帮我订今晚飞成都的机票。”
他不想等24小时。
深夜十一点,他站在一栋老旧居民楼下。陪同前来的是一位当地心理咨询师刘敏,四十岁上下,从事青少年干预工作十余年。她低声介绍:“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在外企做高管,典型‘高期待家庭’。孩子成绩一直年级前十,但从去年开始频繁失眠,体检无异常,医生建议看心理科,家长拒绝,说是‘意志力问题’。”
两人正准备上楼,手机突然震动。后台紧急通知:该账号刚刚上传一段新语音,持续4分18秒,内容判定为极高风险。
林远舟立刻戴上耳机。
男孩的声音极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数学卷子发下来了,我才考了第八名……爸爸看了成绩单,一句话没说,就把我房间的空调关了。他说,冷一点才能清醒。我现在躲在被窝里发抖,不只是因为冷……是因为我觉得,哪怕我拼到死,也不够好。”
>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生病,那样他们就会抱我了。可我又怕他们嫌我麻烦……”
>
>“我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我也不想这样,但我停不下来。”
录音结束,万籁俱寂。
林远舟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类似的面孔??深圳疗养院里的老人、内蒙古牧区的男孩、信阳的周晓雯……他们都曾用不同的方式说同一句话:**我不值得被爱,除非我完美。**
“上去吧。”他睁开眼,声音坚定。
敲门许久,才有一位面容疲惫的中年女子开门。她是母亲。得知来意后,她脸色骤变:“你们凭什么私自调查我家孩子?这是侵犯隐私!”
刘敏上前一步,温和但坚决:“我们不是调查,而是求助。您的孩子正处于严重心理危机中,刚才他亲口说想结束生命。如果我们不来,也许明天就只能由警察来了。”
女人僵住,嘴唇颤抖。
林远舟补充:“我不是要指责谁。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听他说‘我很累’了?”
那一夜,他们四人坐在客厅,谈了整整五个小时。父亲终于承认,自己从小在严苛环境中长大,认为“表扬会让人松懈”;母亲则哭着说,她也曾是优等生,深知竞争残酷,只想让孩子走得更远。但他们从未意识到,那份“为你好”的重量,早已压垮了孩子原本柔软的心。
临走前,男孩悄悄塞给林远舟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谢谢你愿意来找我说话。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死。我只是想歇一会儿,可没人让我停。
林远舟将纸条收进日记本,回到酒店已是凌晨四点。他打开电脑,起草一封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