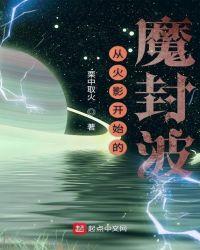笔趣阁>一代兵王从封于修穿越许三多开始 > 第529章 树先生的不正常死亡(第2页)
第529章 树先生的不正常死亡(第2页)
【等待初始信物归位】
李承宇下意识摸了摸手中的“拂晓一号”。
那把扫帚突然微微发烫,杖身上的刻痕泛起金光,仿佛回应某种召唤。
“它要回去了。”封于修说。
“回到哪儿?”
“回到开始的地方。”
他转身指向舰体最深处??那里有一座封闭已久的圆形大厅,门上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地面扫帚划过的痕迹,一圈又一圈,像是某种仪式的路径。
他们走了整整四十分钟才抵达门前。途中经过数十个休眠舱区,里面躺着数百具身穿旧式制服的身影,胸口铭牌写着“轮值人员?乙组”“丙组”……全是上世纪失踪的拂晓先驱者。他们的生命体征极弱,但仍在维持最低代谢,仿佛在等待某个信号唤醒。
“他们也是备份?”李承宇问。
“他们是种子。”封于修纠正道,“每一粒灰里,都藏着重生的可能。”
大门开启时,没有轰鸣,没有闪光,只有一阵风,带着陈年纸张和铁锈的气息扑面而来。
大厅中央,立着一座石台。台上空无一物,唯有一圈凹槽,形状与“拂晓一号”完全吻合。
李承宇走上前,双手捧起扫帚,缓缓将其放入凹槽。
刹那间,整艘“守夜者号”剧烈震颤。
不是爆炸般的冲击,而是如同心脏重启般的搏动,由内而外扩散至每一根结构梁、每一条管线。舰体表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扫”字逐一亮起,从尾部向前推进,宛如黎明破晓时分的第一缕阳光爬过山脊。
星图投影骤然放大,聚焦于地球一处坐标??青海湖畔,当年第一代拂晓基地的遗址。
画面中,荒原之上,一座低矮的土屋静静矗立。屋顶漏雨,墙皮剥落,门前一块木牌歪斜挂着,上面用炭笔写着两个字:
**值班**
屋内,一张破桌,一盏油灯,一本翻开的日志。
镜头拉近,日志第一页写着:
>“拂晓元年,正月初七。
>今日大风,沙进屋三寸。
>扫净。
>封于修,记。”
下一秒,整个页面燃烧起来,火焰呈淡金色,不毁纸张,只将文字逐行蒸发成光点,升腾而起,化作一道信息洪流直冲天际。
与此同时,全球三千七百个心灯站点同步接收到同一段指令代码。无人翻译,无人解读,但所有手持扫帚的人在同一瞬间明白了该做什么。
清扫开始了。
不是为了任务,不是响应号召,而是出于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就像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乱了,就要扫。
东京地铁站,清洁工阿部静子停下推车,默默蹲下,用手帕擦拭一块被踩脏的瓷砖。她不知道为什么流泪,只觉得心里某块堵了很久的东西松开了。
撒哈拉边缘,牧民少年用骆驼毛绑成简易扫帚,一下下扫去观测仪上的沙尘。他说不出科学原理,但他知道,爷爷说过:“仪器干净,星星才看得清。”
纽约中央公园,退休园丁詹姆斯带着孙子清理喷泉池底的落叶。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干这么累的活,他笑着说:“因为有人曾经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这些动作微不足道,分散各地,看似毫无关联。但在拂晓系统的维度中,它们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共振波。
【全域清扫频率达成临界值】
【三位一体验证通过】
【‘归墟重启协议’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