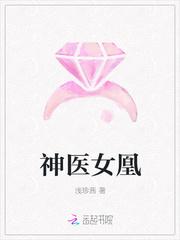笔趣阁>活人深处 > 第776章 二对一(第3页)
第776章 二对一(第3页)
而在手册末页,有一行手写批注:
>“我们以为控制声音就能控制人心。
>却忘了,真正可怕的力量,从来不是呐喊,而是长久沉默后的第一声低语。”
妹妹看到这句话时,久久无言。
她想起小时候,祖母常带她去老城区散步。某天路过一所废弃小学,墙上爬满藤蔓,教室窗户碎裂。祖母停下脚步,指着一间教室说:“那里曾经有个女孩,每天放学后都留下来唱歌。她妈妈说她五音不全,同学笑她吵闹,老师让她闭嘴。但她坚持唱,直到毕业那天,整栋楼的学生都站在窗外听完了最后一首。”
“后来呢?”她问。
“后来学校拆了,歌声也没了。”祖母轻声说,“但你知道吗?去年我路过这里,听见风穿过窗框的声音,居然和她唱的调子一模一样。”
当时她不懂,现在明白了。
有些声音不会死去。它们只是暂时沉睡,等待被重新唤醒。
一个月后,联合国宣布成立“全球情感遗产委员会”,正式将静语系统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此同时,第一批“共感教师”开始进入校园,教授孩子们如何识别、表达、接纳复杂情绪。课程不用考试,唯一的作业是每周写一封信给“未知的倾听者”。
妹妹受邀参与课程设计。她只提了一个要求:每间教室都要设一座微型静语亭,无论大小,无论装饰,只需保证隐私与安全。
“教育不该只是传授知识,”她在提案书中写道,“更是教会孩子??当你感到痛苦时,不必忍耐;当你想要爱时,不必羞愧;当你有话想说时,永远有人准备聆听。”
项目落地那天,她回到南太平洋孤岛,却发现海滩上多了一座新建筑??不大,灰白色墙体,圆顶,门前立着一块木牌,写着:“第一所共感学校试点”。
推门进去,教室中央摆放着一台老旧录音机,正是当年祖母实验室里的型号。旁边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上面是孩子们稚嫩的笔迹:
>“今天我告诉静语亭,我很怕黑。晚上睡觉时,它给我放了一首摇篮曲。”
>
>“我说我想爸爸了。第二天,有个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也想她的孩子。”
>
>“我以前觉得没人懂我。现在我知道,只要我说出来,就会有人懂。”
她站在门口,泪水滑落。
辛-001走来,递给她一杯热茶。“你说过,活人深处不是地方,不是技术,是一种状态。也许……我们正在一点点接近它。”
她点点头,走到录音机前,按下播放键。
里面传出一段熟悉的童谣,由不同年龄、不同口音的人接力演唱,温柔而坚定。唱到最后,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星星眨眼睛,
>月亮照心房,
>只要你说出真心话,
>黑暗也会发光。”
歌声结束,录音机自动倒带,准备迎接下一个声音。
她转身走出教室,抬头望向天空。极光悄然浮现,不再是耳廓形状,而是一张张张开的嘴,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低语。
她知道,这场对话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在地球某个角落,总有一个人,正鼓起勇气,准备说出第一句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