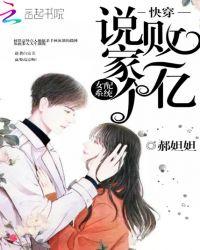笔趣阁>重启人生 > 0495请小日子当美国子公司的CEO(第2页)
0495请小日子当美国子公司的CEO(第2页)
深夜,系统再次弹出通知:山东少女第二次面谈完成,情绪明显好转,主动提出想参加线上写作小组。她交给咨询师一本日记,最新一页写着:“今天我对食堂阿姨说了‘麻烦您多给点菜’。她笑了,真的多给了我一勺土豆丝。原来被人回应的感觉……像太阳照进碗里。”
许风吟看着这条反馈,忍不住笑出声。他打开邮箱,给她回了一封简短的信:
>“亲爱的你:
>那勺土豆丝,是你为自己争取的第一缕光。
>它很小,但足够温暖一顿饭的时间。
>而一顿饭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决定再活一天。
>继续写吧,继续说吧,继续要那勺菜吧。
>世界正在一点点为你变软。
>??许风吟”
第二天清晨,他照例查看日总结报告。新增数据中有一条引起注意:一名来自广西百色的用户,连续五天上传同一句话的不同写法??
第一天:“我不想活了。”
第二天:“我……不想……活了。”
第三天:“我……不想……活……了。”
第四天:“我……想……活……吗?”
第五天:“我……还能……活……下去吗?”
许风吟立即调取信息:十七岁女生,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十年,由爷爷奶奶抚养。曾因成绩下滑遭老师当众批评“没家教”,从此拒绝上学。历史记录显示,她最早的一封信写于半年前,标题是《我是一块被遗忘的橡皮》。
他没有立刻回信,而是先联系当地妇联合作的心理老师黄丽娟。两人商议后决定:由黄老师先行家访,建立信任;许风吟则准备一封“过渡性回信”,不急于劝解,只承认她的挣扎。
当晚,他写下:
>“亲爱的你:
>我看到了你这几天写的字。
>那些越来越长的省略号,像不像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着往前走?
>每一步都犹豫,每一脚都怕踩空。
>可你还在走。
>甚至开始问自己:‘还能活下去吗?’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希望的芽。
>
>我不知道你的世界有多冷。
>但我知道,当你写下这些字时,心里一定还留着一小块地方,盼着有人能懂。
>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
>我懂。
>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也曾把自己缩成一句话,再缩成一个词,最后只剩下一个问号。
>
>你现在不需要马上相信未来。
>只需相信一件事:
>你有权感到痛苦,也有权寻求帮助。
>就像迷路的孩子可以问路,饿了的人可以讨一口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