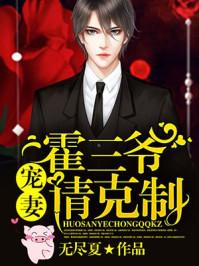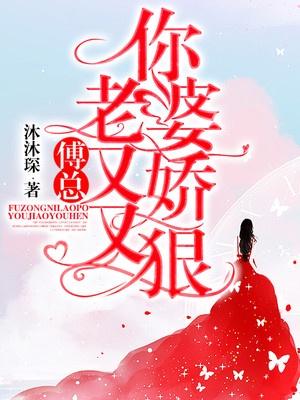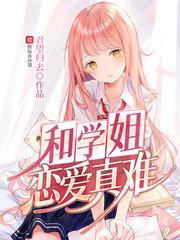笔趣阁>虎贲郎 > 第727章 前程焦虑(第2页)
第727章 前程焦虑(第2页)
韩岱怒极,拍案而起:“他终于撕下面具了!现在怎么办?迎战?还是撤入山中?”
赵承却神色不动,反而笑了。“他急了。说明我们的文章,比他的刀更快。”
他转身取出早已备好的另一份文书??《北疆共盟誓约》正本,盖有十七个部族图腾印鉴、三百余名村老联署签名、以及共盟议会全体成员血书按印。
“从今日起,晋阳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姓王朝。”赵承朗声道,“它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不再是将军,只是你们的同行者。若贾充敢来,我不以兵拒之,而以民阻之。让他看看,什么叫‘民心不可辱’。”
命令迅速下达:全城戒备但不开战;所有官署照常办公;百姓照常劳作;学堂照常授课。唯独城门口竖起一面巨幅白布,上书八个大字:
**“无将军,有共盟”**
与此同时,林照儿组织医馆全员进驻城南窑区,设立临时病房,收治老弱病残;阿塔尔率领少年巡防团日夜巡逻,维持秩序;阿兰朵奔走各胡族营地,确保部族团结一致。更有无数普通百姓自发行动:农夫们将粮食藏入地窖,工匠们拆卸兵器藏于墙夹层,妇女们缝制旗帜与袖章,上面写着“归来即同胞”“守望相助”等字样。
第三日,贾充大军抵近城郊。队伍整齐,旌旗猎猎,气势汹汹。然而当他们靠近西门时,却发现道路已被数百名老人、妇孺和孩童占据。他们手挽着手,席地而坐,面前摆着饭篮、水壶与草鞋。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颤巍巍站起,高声道:“我家儿子死在鬼哭峡,仇人是兀烈,不是赵将军!你们说他是叛臣,可他给我们田种、给孩子书读,让我们活得像个人!你们若要抓他,先踏过我们的尸体!”
人群齐声呐喊:“无将军,有共盟!不许动晋阳!”
贾充怒极,下令驱散。士兵上前推搡,几名老人跌倒受伤。就在此时,数十名少年巡防团成员冲出巷口,手持木棍,列阵阻挡。紧接着,更多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却没有一人率先攻击。
场面僵持整整一日。直到夜幕降临,贾充不得不下令后撤十里扎营。
赵承当晚登上城楼,面对万千民众,缓缓摘下腰间佩刀,置于石台之上。
“这把刀,随我十五年,斩敌无数。”他声音沉稳,“但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它。因为保护这座城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武力,而是所有人共同的意志。”
台下寂静无声,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喊。人们流泪相拥,许多胡族战士跪地叩首,以草原最隆重的礼仪向这位汉人将军致敬。
第七日,边关传来惊人消息:鲜卑东部大人轲比能率三万骑兵南下,宣称“助晋阳守义”,已攻破贾充后方补给线,截获粮草辎重无数,并留下一句话:“赵将军葬我族死者,教我女儿读书。今日,轮到我们还债。”
消息传开,举世哗然。连司马懿也不得不下令召回贾充,暂缓行动。
赵承并未因此松懈。他知道,真正的战争不在战场,而在人心深处。他召集共盟议会,宣布启动“千村筑学计划”:三年内,在北疆每一座村落建立学堂,无论胡汉,儿童六岁入学,学习识字、算术、农技与《约章》。师资由共学书院统一培训,经费来自技工坊盈利与民间募捐。
同时,他致信各地义士,提出“联义共治”构想:凡愿推行仁政、保障民权、尊重共盟原则之地,皆可加入北疆同盟,共享技术、互市通商、遇危互助。信末写道: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万民之天下。
>若王者失道,诸侯可谏;诸侯失德,百姓可择。
>我等所求,非割据称雄,惟愿人间少一分苦,多一点光。”
春去秋来,晋阳城外稻谷飘香。共学书院如期建成,首批三百学子入学,其中包括四十名女子与六十七名胡族子弟。开学当日,赵承亲自授课,题目是《何谓君子》。他说:
“君子者,非生于庙堂,而起于阡陌。能悯人之苦,敢言人之不敢言,行仁于细微,守信于危难??此即君子。你们不必成为达官显贵,只要成为这样的人,便足以照亮一方天地。”
课毕,学生们放飞千纸鹤,每一只翅膀上都写着一个愿望。有“愿母亲不再咳血”,有“愿草原不再打仗”,也有“愿我能当女医师”。
林照儿站在人群中,看着漫天飞舞的白影,忽然落下泪来。
赵承走到她身边,轻声问:“怎么了?”
“我在想娘。”她擦去泪水,“她说医者治得了病,治不了世道。可现在,我觉得我们在一点点治好这个世道。”
赵承握住她的手,望向远方。
夕阳之下,麦浪滚滚,纸鸢依旧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