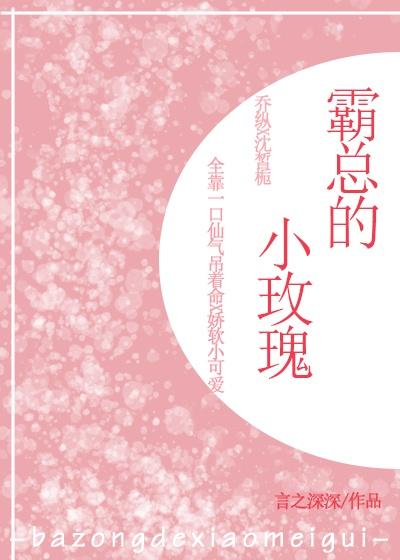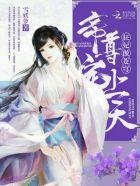笔趣阁>虎贲郎 > 第740章 大岘山西(第2页)
第740章 大岘山西(第2页)
众人无不落泪。
与此同时,晋阳书院迎来一批特殊访客??三十六名曾被列为“逆党家属”的妇女。她们来自不同州郡,丈夫或儿子或因言获罪,或死于冤狱,多年来隐姓埋名,苟活乡野。
林照儿亲自主持接待。她请她们讲述亲人故事,并安排学子记录成册。一位老妇颤巍巍地说:“我夫君是洛阳太学助教,只因私下议论‘崔胤专权’,便被削籍流放岭南。五年后,我收到一包骨灰,说是病故。可同去之人后来逃回,告诉我他是被活埋的,因为不肯写下‘悔过书’。”
另一名少女泣不成声:“我哥哥十三岁,抄了一段《双玉冤录》贴在村口,当天就被抓走。三个月后,县令说他‘畏罪投井’。可我知道,他最怕水,连洗澡都不敢下池。”
这些证词被整理为《沉默者之声》,印刷三千册,分送各地官府与书院。更有巧匠将其制成盲文版,送往各地瞽目学堂。
此事震动朝野。御史台被迫重启调查程序,追责二十七名在职官员,其中九人主动辞职。皇帝亦下诏:“凡涉言论旧案,无论已结未结,一律重新审查,不得以‘时过境迁’为由推诿。”
就在舆论沸腾之际,意外再生。
一名自称“张让家仆”的老人出现在长安街头,手持竹筒,内藏一份泛黄手札。他说,张让临终前曾口述遗言,由他秘密抄录,藏于瓦罐埋于后院,直至近日才敢取出。
内容令人震惊:
>“吾一生侍宦,深知宫闱黑暗。崔胤固然是奸,然陛下亦非无辜。贞观十七年之事,实为帝心默许。彼时帝患重疾,恐权归外戚,故借崔胤之手铲除异己,再以‘清君侧’名义诛之,一举两得。梁承业之女阿兰朵,确被囚禁,然非为阻和议,实因其掌握先帝遗诏??立庶长子为嗣,而非当今。此诏若现,江山易主。故必灭口,伪称暴毙……”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赵明远接到快报时,正坐在书院廊下校阅《续编》稿件。他读完一遍,又读第二遍,脸色愈发凝重。
“若属实……”陈知微声音发抖,“那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在庙堂之外,而在龙椅之上。”
赵明远久久不语。良久,他提起笔,在纸上写下四个字:“真相代价”。
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当信义运动从反抗压迫走向直面历史核心,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最高权力本身便是罪恶源头,我们是否仍有勇气揭穿?
三日后,他召开紧急会议。赫连曜尚未归来,阿兰朵音信全无,唯有林照儿与几位老臣在场。
“公布吗?”有人问。
“不。”赵明远摇头,“现在公布,只会引发动荡。百姓刚尝到言论自由的滋味,若突然得知皇帝竟是始作俑者之一,恐怕会彻底失去对制度的信任。我们要的不是颠覆,而是进化。”
“那怎么办?”
“我们将这份遗言封存,交由即将成立的‘信义史馆’保管,并立下铁律:除非三代之后,且国家实现完全宪治,否则不得开启。”
“可这就成了新的隐瞒!”一名青年学子激动起身,“我们一直在呼吁说真话,如今却自己藏起最关键的真相!”
赵明远看着他,眼神温和却坚定:“你说得对。这是背叛,也是保护。就像父母不会对五岁孩童讲述战争的全部血腥,不是欺骗,而是等待他长大。今天的百姓,还没有准备好承受那样的冲击。但我们必须留下线索??让后人知道,这里有一块不能碰的石头,下面压着什么。”
于是,他们在晋阳书院后山立起一座奇特石碑:通体漆黑,无字无铭,仅在基座刻一行小字:“此处封存一段足以动摇国本的真相,待后世智勇兼备者启之。”
此举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称其为“智慧的克制”,反对者斥之为“懦弱的妥协”。连一向温和的郑伯昭也叹息:“赵兄,你今日埋下的,或许是百年后的雷。”
赵明远只答一句:“若我不埋,今日就会炸。”
风雨再起。
一个月后,赫连曜终于归来,带回惊人消息:西域十二国一致同意签署《丝路信义公约》,承诺今后争端不由刀兵解决,而提交“跨域信义法庭”裁决;同时,龟兹回音铜镜已被复制五面,分别安置于撒马尔罕、巴格达、长安、敦煌与建康,形成“共鸣网络”,确保任何重要誓言都能跨越时空传递。
“更关键的是。”赫连曜压低声音,“我们在龟兹密档中发现了当年北疆军阀与波斯商人勾结的账册,上面清楚记载:崔胤家族通过走私军械积累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至今仍藏于洛阳某座废弃佛塔地宫。”
赵明远闻言,立即下令彻查。三个月后,地宫开启,出土黄金三千斤、珠宝无数,更有大量契券显示这些资产早已转入民间商会,渗透进粮盐铁三大命脉。
证据呈报朝廷,皇帝震怒,下令全面清查经济系统,罢免十三名高官,其中包括两名尚书省侍郎。
至此,信义运动不仅改变了政治生态,也开始重塑经济秩序。
然而,赵明远的身体却日益衰弱。风湿侵骨,行走艰难,夜间常咳出血丝。医生劝他静养,他却笑言:“我的命早就该结束在十五年前的那个雪夜。多活这些年,已是上天厚待。”
这一年冬至,他坚持登上思子台,亲手点燃第一盏灯笼。随后,晋阳万家灯火齐明,空中浮现巨大的“信”字光影,一如十年前初胜之时。
但这一次,没有欢呼,只有静默。人们围坐家中,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沉默者之声》录音,那是盲童们用稚嫩嗓音诵读的遇难者遗言。
赵明远坐在台上,听着风中的诵读声,轻轻抚摸那支斑驳竹笛。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制度可以建立,法律可以颁布,碑林可以矗立,但真正的信义,永远生长在每一个普通人选择不说谎的瞬间。
他抬头望天,细雨又起。
像十年前一样,温柔,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