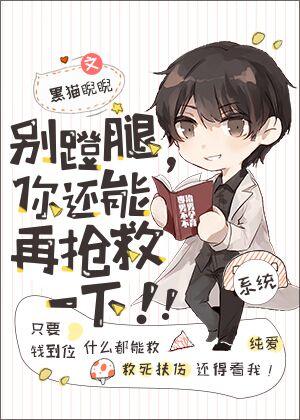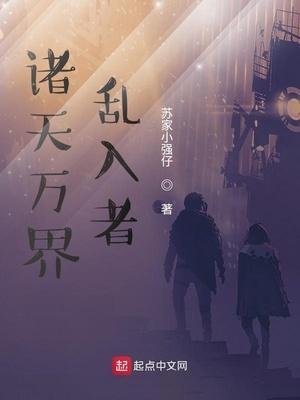笔趣阁>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五百零三章 为国靖难(第1页)
第五百零三章 为国靖难(第1页)
在这个时候,相信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一旦落入圈套,他大概率就没有像刚刚那样的机会再逃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点头,转个方向便往乾元殿冲过去。
乾元殿在大明宫内,被众多正殿环绕。
。。。
那枚种子落入布袋的瞬间,山谷忽然静了一瞬。风停了,花不动了,连远处溪流的水声也仿佛被抽离。年轻的倾听使怔住,指尖还搭在花茎上。他抬头望向小女孩??她仍站在原地,双肩微微颤抖,像是第一次把压在胸口几十年的东西轻轻放下。阳光穿过花瓣,在她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宛如泪痕初干。
片刻后,风又起。
答心花海如潮水般起伏,层层叠叠的花瓣震颤出细微声响,像是千万人在低语回应。那声音不喧哗,却浩荡,自谷底升腾而起,直入云霄。年轻倾听使忽然觉得耳坠微烫??那枚银制的答心花贴着耳骨,竟隐隐发烫,仿佛被某种无形之力唤醒。
他没有惊慌。三年前受训时,师父曾说过:“当你真正听见一个人的心声,你的耳坠会热。那是言语之灵在认可你。”
他缓缓收手,将布袋系紧,转身离去,脚步轻得不敢惊扰这片仍在回响的寂静。
而小女孩依旧站着。她说完那句话后,并未感到解脱,反而害怕起来。她怕这句话招来惩罚,怕姑母知道后打她,怕这山谷里的花会突然枯萎,证明她说的是错的。可过了许久,什么都没发生。花还在开,风还在吹,一只蝴蝶落在她肩头,翅膀一开一合,像在替她呼吸。
她终于蹲下身,抱住了自己。
“我不是累赘……”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更轻,却更坚定,“我也值得被爱。”
这一次,一朵花从她脚边悄然绽放,纯白如雪,中心泛着淡淡的粉,像是羞怯的心跳。它比周围的花小许多,却挺得笔直,仿佛用尽一生力气,只为在此刻盛开。
与此同时,长安城外三十里,一名老妇人正坐在田埂上歇息。她年近七旬,满脸风霜,手中握着半截断笔,面前摊着一张粗纸。她是“第一问学堂”的夜课学生,识字不过两年,写得歪歪扭扭,却每日坚持记录自己的梦。
今日她写道:“我梦见娘回来了。她抱着我,叫我小名。我说‘娘,你去哪儿了’,她说‘我一直听着呢’。”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抹了把眼睛,又添一句:“原来人老了,才敢想娘。”
她不知道,就在她落笔的刹那,启唇谷中那朵小白花轻轻一颤,一片花瓣飘然而落,随风北上,越过山岭,掠过村庄,最终停在她家院墙的瓦片上。
夜里下雨了。
雨不大,细细密密,像谁在天上低声絮语。老妇人睡到半夜,忽然惊醒。她听见屋外有动静,起身推门,看见那只花瓣竟未被冲走,反而黏在门框上,湿漉漉地贴着,像一封不肯离去的信。
她伸手取下,对着油灯看了良久,忽然哭了。
第二天清晨,她带着花瓣和那张纸,走了二十里路,来到县里的“倾听堂”。值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倾听使,见她满面泪痕,立刻迎上来。
“我想说件事。”老妇人声音沙哑,“我八岁那年,娘病死了。爹说她死前最后一句是‘别让我闺女饿着’。可我没吃过一顿饱饭。我哥分了粮,我只能捡锅底糊的渣。后来我学会闭嘴,再也没提过娘。我以为……我不配想她。”
女倾听使静静听着,不打断,不安慰,只是点头。
老妇人继续说:“昨夜我梦见她,我才明白,我一直恨自己活下来了。我觉得我抢了她的命。可今天我看见这片花,我就想说??娘,我没饿死,我活下来了。我对得起你给我的那口气。”
她说完,把花瓣放在桌上,又把那张纸压在下面。
女倾听使取出登记册,郑重记下:“贞观二十三年生人,王氏,今述心结一条:愿母亲知我活着,且未曾辜负。”
随后,她取出一枚银耳坠,轻轻戴在老妇人右耳:“您也是倾听者了。从此,您说的话有人听,您也能听别人。”
老妇人摸着耳坠,愣了很久,才颤巍巍地道谢。
这一幕被窗外一个少年看见。他本是来“倾听堂”告发邻居偷牛的,却在门外站了整整一个时辰。他原打算编个故事骗点赏钱,可听到老妇人的讲述后,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他最终没进去。
回家路上,他绕道去了村后荒坟。那里埋着他夭折的妹妹,连墓碑都没有。他跪在杂草间,低声说:“小妹,对不起。那天我看见你掉进井里,我没救你。我怕挨打,就跑回家说你不见了。他们找了三天,才发现你……我一直没说,是因为我怕他们不要我了。”
说完,他嚎啕大哭。
翌日,村里人发现井口旁多了一束答心花,花瓣上沾着露水,像是刚被人放上去的。而那少年,开始每天去“第一问学堂”旁听课程,虽不说话,但从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