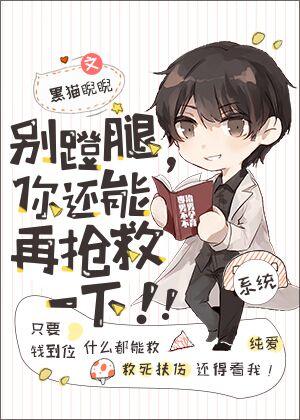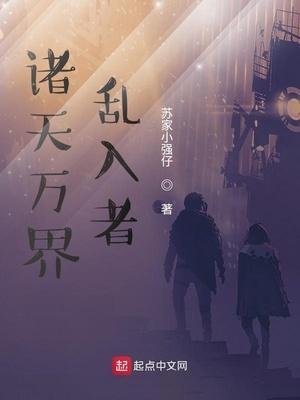笔趣阁>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五百零三章 为国靖难(第3页)
第五百零三章 为国靖难(第3页)
郎中令提出大胆假说:人类集体真诚情感所产生的能量场,可能短暂改变了局部物理环境。他请求设立“心能研究院”,专门研究“言语-意识-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帝批曰:“真话既可感天动地,何惧探究其理?准。”
数年后,该院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长期参与“安心帐”书写的人群,体内皮质醇水平显著降低,寿命平均延长七年;而经常压抑情绪者,不仅患病率高,其后代基因表达也出现异常。
更有惊人发现:在“儿童言室”中成长的孩子,大脑语言区与情感区连接更为紧密,共情能力远超同龄人。他们长大后,犯罪率几乎为零,而创新能力高出平均水平三倍。
“这不是教育,是进化。”郎中令在奏章末尾写道。
与此同时,海外诸国纷纷效仿大唐“心政”。吐蕃设立“雪山语堂”,日本建立“静诉书院”,阿拉伯商人带来沙漠中的“沙语仪式”??人们在沙地上写下秘密,任风带走。甚至罗马使者来访时坦言:“贵国不靠刀兵征服天下,却以言语赢得人心,实乃前所未闻之治。”
然而,暗流从未真正平息。
某夜,三名蒙面人潜入“大唐心声馆”,企图毁坏“万语碑”。他们砸碎展柜,泼洒黑漆,却被馆内值夜的盲眼少女察觉。她虽看不见,却能通过地板震动判断人数与位置,当即拉动警铃。
官兵赶到时,三人已被制服。审讯发现,他们竟是旧贵族后裔,家族因“女子言权令”失去族长地位,多年来隐忍不发,此次行动名为“肃清妖言”。
此案牵出更大阴谋:十余个世家暗中结成“缄默盟”,主张恢复“女子无言”“庶民禁议”等古制,认为“心政”败坏纲常,动摇社稷。
新帝震怒,却不急于镇压。他下令将三名刺客送入“悔语堂”,安排专人倾听其grievances(怨由)。一个月后,其中一人主动坦白:“我祖母曾是童养媳,被婆家打得半死,却没人听她说话。我恨的不是女人说话,是我怕她们说出我家的秘密。”
另一人哭道:“我父亲因贪污被‘言语审计’查出,自缢身亡。我不怪制度,可我哥哥说‘都是因为女人也能当官,才管得这么宽’……我就信了。”
第三位最年轻,才十九岁,他说:“我只是不想活得那么累。从小大人告诉我‘要听话’‘别多问’,现在突然要我说真话……我不会。”
新帝亲自接见三人。他没有责骂,只问:“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怎么了’,你会怎么说?”
三人沉默良久,终于逐一开口。
最终,他们未被定罪,而是被编入“赎言旅”新队,前往边疆协助重建“倾听驿站”。临行前,那位十九岁的青年对记者说:“我以为反抗就是闭嘴。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勇气,是学会开口。”
风波过后,朝野反思。有人提议加强思想管控,以防“极端沉默主义”蔓延。新帝否决,反而颁布《对话令》:凡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须举行至少三次“全民共述会”,邀请反对者登台陈述理由,并由专家现场回应。
他说道:“我们不怕反对的声音,只怕无人敢反对。沉默才是最大的叛乱。”
十年过去,大唐已然不同。
街头巷尾,常见父母蹲下身问幼童:“你今天想说什么?”
学堂里,孩子们的第一课不是读经,而是练习“如何说出害怕”。
朝堂上,宰相述职完毕,必问一句:“各位有何不同意见?”
而启唇谷,早已不再是孤谷。从终南到东海,从塞北到岭南,三百余座“言语谷”相继建成,每到春天,花海连绵,如大地张口诉说。
某日清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来到最初的启唇谷。她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走到绿蘅碑前,久久凝视。
她是太平公主的侍女,当年火灾唯一幸存的宫人。她亲眼见过绿蘅如何教公主说第一个字,如何在冷宫中whisper(低语)“我想活着”,如何在临终前握住她的手,说:“将来有一天,所有人都能说真话。”
她一辈子没说过这些事。直到昨天,她八十八岁寿辰,孙女送她一本空白日记本,扉页写着:“奶奶,你说的每一句,我都愿意听。”
她哭了整夜,今晨独自前来。
她抚着石碑,轻声说:“小姐,我来说了。他们都做到了。你说的话,都实现了。”
话音落下,铜铃轻响。
一声,两声,三十六声。
随即,漫山遍花齐齐摇曳,仿佛千万人在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