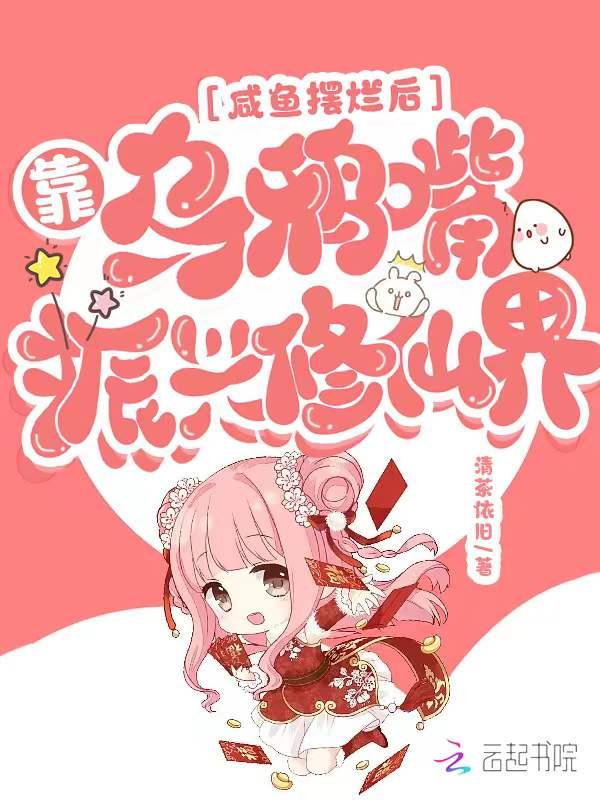笔趣阁>在西汉庖厨养娃 > 8090(第27页)
8090(第27页)
“我有!”
只见季止返身进至西屋,从床底下的老鼠洞掏出个钱袋,倒出来一堆五铢钱,有五十个。
这都是从前她做小买卖,背着金氏,每日抠出来一点攒下的。
金氏给她头上戳了下,骂道:“死丫头竟敢背着我藏私房钱,我不说盘缠不够你也不拿出来了,放你那丢了可惜了,都拿给我管。”
说罢也不客气,将那钱都搂过来收着了。
季止在一旁垂手站着,瞧着眼巴巴的,身上的肉疼。
又听金氏道:“这些还不足,听说办传要些时日,趁这日子,将家里那二十亩地卖了。”
次日早,季富仍塞了嘴捆在西屋,金氏携二女,去乡啬夫那办理了前往邯郸的传,外出缘由是寻子、投靠亲戚。
只是家里二十亩地,本就不算上等良田,只能算中等,加之卖的急,只卖了十八两。
外人见她卖地,也有疑心的,只是听说她丢了孩子,才变卖家产以找寻,倒也谅她这份急切的心。
也有问:“你家季富呢?几日不见他了,卖田这样的大事他竟不来?”
金氏诌道:“县里找了份车夫的活计,并不回家住了。”
众人便信服了。
待到七日后,一乡亲拿着金氏临走托付的钥匙,将大房门解开,不防被吓了一跳。
季富躺在地下,瘦了一圈,屎溺一地,见人来在地下蛄蛹,身上的骚臭味熏的人掩鼻直退。
那乡亲忍住恶心,替他将那团堵口的抹布抽出来,只听他道:
“报官……我要报官……”
那毒妇,每日只给他吃个豆脯,怕他尿多,连水也给的有限,这会子他的喉咙哑的连话也说不全。
话说季胥一行。
因和车父一队相伴,安全的行路千里,途径寿春、合肥等地,到了彭城附近。
三千余里路,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实在是件可喜之事。
彭城附近水道交纵,陆路不能通行,她们便改乘船只进城地界。
只见津渡停有许多渔翁打扮的百姓,有的撑竹筏。
有的则撑木罂缻,季胥没见过这样的,多看了两眼。
只见是一种底下连着空心的水葫芦,上面缚块木板,利用水葫芦的浮力,能容纳三四人的小舟。
篙人在津渡口以摆渡谋生,进城一趟按人头算钱,素日大人十钱,小孩五钱。
季胥姊妹仨,加一辆牛车,一只独筏坐不下,那掌篙的老翁道:
“这样,小郎你雇我们两家的,我们中间搭木板,固定在木罂缻两头,结驷而行,足能载重你一家。”
“好。”
季胥便雇了两只木罂缻,结驷并渡,妹妹们将布橐或抱或背,坐在中间。
因这牛没渡过河,怕它发狂,季胥按老翁教的,用一块巾子蒙住了它的眼,跟在一旁稳住它。
车父那行戍卒,则雇了三只竹筏结驷,连人带牛车,也渡水进城了。
凤、珠两个在水上东瞧西望,满眼新奇。
只见那彭城依水而建,水道直通城内,她们竟是坐在木罂缻上,一路划进城的。
连那城门吏查看她们的传,也是坐在舟上,将木楫打横过来接递的。
城内水浮陆行,水上唱棹,岸上转毂,士女商贾,苎衣绮服,行路杂沓,看的人眼花缭乱。
“嚯!瞧那大家伙!”季凤惊呼道。
“那是楼船。”撑篙的老翁笑道。
只见一艘足有四层楼高的楼船举帆入内,那白帆尖,远远看着几乎剐蹭到城门洞的拱顶,待走近了,只见船板上倡优啁戏作乐,依稀可见船内公子哥把酒言欢的身影。
跟那楼船一比,季胥她们乘的木罂缻就和蚂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