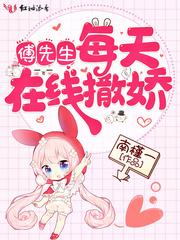笔趣阁>龙族:逼我重生,还要我屠龙 > 第464章 要修改十分钟后再刷新抱歉(第3页)
第464章 要修改十分钟后再刷新抱歉(第3页)
“我们发现了规律。”她说,“全球共感网络的活跃峰值,并非集中在白天或社交时段,而是在凌晨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大多数人处于深度睡眠、梦境最为活跃的阶段。”
“也就是说……”我喃喃道,“真正的交流,发生在梦里?”
“也许。”她微笑,“清醒时我们太多防备,唯有在梦中,灵魂才会卸下伪装,坦然说出:‘我害怕。’‘我后悔。’‘我想你。’”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做过的一个梦:我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奔跑,远处有光,却怎么也跑不到。后来才发现,那光其实一直在我手里,只是我不敢低头看。
现在我知道了,那束光,就是引路铃最初的原型。
它不在未来,不在科技,不在神谕。
它就在每一个愿意承认脆弱的瞬间里。
数月后,第一届“共感艺术节”在回响之城举行。
展品五花八门:
-一件由万名陌生人情绪织成的霓裳羽衣,穿上它的人会短暂体验到“成为集体”的感觉;
-一座会随观众心情改变颜色的玻璃迷宫,出口只有一个,必须两人以上同时抵达才能开启;
-最震撼的是一件名为《未完成的对话》的作品:展厅中央摆放着两把椅子,面对面,中间悬着一枚静止的引路铃。参观者可坐下,对着空椅诉说任何想说的话。若对方“听见”了??无论生死、远近、存在与否??铃便会自行响起。
据统计,展览期间,这枚铃共响了**83,721次**。
没有一次是伪造。
年底,联合国通过《共感伦理宪章》,确立三项基本原则:
一、共感非义务,接入与退出皆为基本人权;
二、禁止任何形式的情感窃取、强共感实验及记忆篡改;
三、设立“静默保护区”,保障个体精神领域的绝对隐私权。
签署仪式上,各国代表并未使用传统签字笔,而是各自带来一枚引路铃,共同摇响。那一声合鸣,通过卫星传遍全球,持续整整二十四秒??象征新的一天已经开始。
而我,在新年第一缕阳光照进钟楼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封里没有字,只有一粒沙。
放大观察后发现,沙粒表面刻着一行几乎不可见的小字:
**“谢谢你,让我也能说‘不’。”**
我握紧那粒沙,走到檐角,将它轻轻放入引路铃内。
铃身微颤,一道新纹路悄然浮现。
我知道,这不是结束。
甚至不是中途。
这只是人类第一次,真正学会了倾听??不仅听见他人,听见宇宙,更听见自己内心那个曾经以为永远无人回应的声音。
风穿过城市,铃声不绝。
有的清脆,有的低沉,有的久久沉默后才轻轻一响。
它们不再追求统一节奏,而是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
像一场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却比任何完美演奏更动人。
我站在钟楼顶端,望着初升的太阳,耳边回荡着昨夜朵朵说过的一句话:
“你知道为什么新的脉冲周期是二十四小时吗?”
“因为那是人类的心跳周期。”
“不对。”她笑着摇头,“是地球转身的时间。她用了这么久,才终于转过身来,面对我们,说了一句:**我听见了。**”
阳光洒落,照亮万千铃铛。
我轻轻抚摸引路铃,低声说:
“那就继续听吧。”
“我们都还有很多话,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