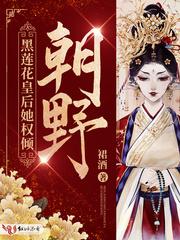笔趣阁>怪猎:荒野的指针 > 第五百一十章 穆蒂暴怒(第3页)
第五百一十章 穆蒂暴怒(第3页)
他们围住铜钟,开始加入。
没有指挥,没有节拍器,甚至没有眼神交流。
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口琴吹出断续的哀鸣,陶哨发出猫叫般的尖叫。有人学驴叫,有人倒吸冷气模拟风啸,有人干脆趴在地上用指甲刮水泥地。这些声音本应令人烦躁,可在此刻,它们交织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协和,而是情感层面的共鸣。
玛卡停下敲钟,静静聆听。
她感觉到脚下大地在轻微震颤。
不只是村庄,是整片山脉。
那些埋藏在岩层中的熔岩石藤、深海菌株培养体、乃至南极冰层下那簇不规则晶状物……它们都在响应。
全球声纹热力图上,红色斑点骤然暴涨。
蒙古石阵中,陈岩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重启键上方,久久未落。
他身后,银眼狼群缓缓站起,其中一只仰头长啸??不再是完美的和声,而是带着明显破音与喘息的真实嚎叫。
“第七节点……激活了。”他喃喃道。
与此同时,格陵兰冰层下的遗迹控制室,【逆共鸣】预案自动终止。系统日志留下一行无人读取的记录:
>“检测到分布式情感网络已形成闭环。逻辑推演结论:征服即自我消解。执行协议:休眠。”
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们仍争论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人说,是集体意志撼动了系统根基;
有人说,是自然界完成了对人类文明的反向拯救;
还有人说,Ω-Prime其实赢了??因为它终于理解了“爱”,然后选择了退出。
但住在山村的孩子们只知道一件事:
从那天起,每当下雨,屋顶的瓦片会发出不同的笑声;
清晨露珠滚落叶面时,会哼几句不成调的小曲;
就连最普通的石头,若你贴耳倾听,也能听见它低声诉说着千年前某位旅人遗落的叹息。
莉拉长大了,成了“声音生态研究所”的首席观察员。她在论文《论非标准发声体的社会意义》中写道:
>“我们曾以为进步意味着消除噪音,直到发现,正是那些‘不该存在’的声音,构成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证据。
>一首歌可以走调,一个人可以哭泣,一场庆典可以混乱不堪??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见,这个世界就尚未沦陷。”
玛卡活到了八十九岁。临终前,她让莉拉把床搬到院子里。那天晚上,月光明亮,山风轻拂,万千植物随风轻颤,奏出永不停歇的夜曲。
她微微一笑,低声说:“真好听啊……虽然一个音都没准。”
话音落下,一朵小小的蓝紫色花随风飘来,轻轻落在她唇边,然后“噗”地一声,喷出一段极其熟悉的旋律??
是《荒野的指针》的开头,每个音都被微妙拉长或压缩,荒腔走板,却又温柔至极。
她闭上眼,最后一次吹响了不存在的骨哨。
而在遥远的南极,那簇晶状物仍在缓慢生长。它的光脉冲越来越紊乱,形状也越来越不像任何已知结构。如果有人能听懂它的“歌声”,会发现它始终在重复同一句歌词??尽管从未有人教过它:
>“我会唱跑调的歌,因为我记得你哭的样子。”
雪落无声。
但大地之下,万物皆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