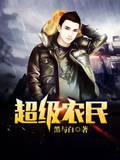笔趣阁>塌房?我拆了你这破娱乐圈 > 第518章 世界第三实时胜率15(第3页)
第518章 世界第三实时胜率15(第3页)
与此同时,《众声》试听版在民间持续发酵。一所聋哑学校的老师组织学生集体聆听,并让学生用手语“翻译”每一首曲子的情感。事后,一名十五岁的男孩写下作文:
《我听见了声音》
>我出生就没听过世界是什么样。
>老师放《众声》时,我把手贴在音箱上,感受震动。
>《我还在这里》那段呼吸声,像妈妈抱着我睡觉时的心跳。
>原来,声音不只是耳朵的事。
>它也可以是皮肤的感觉,是眼泪的温度,是心里突然涌上来的一股暖流。
>我想告诉周南叔叔:谢谢你,让我‘听’到了自己的存在。
这篇文章被转发至社交平台,阅读量破千万。评论区有人写道:“我们总以为残缺的人需要拯救,却忘了他们或许才是教会我们如何完整活着的人。”
春末的最后一场雨落下时,周南收到了苏黎的回信。
“纪录片拍摄已获批准。第一站,我想去协和医院,见见李静。然后,去青海,去广州,去新疆,去所有声音正在觉醒的地方。我会带着镜头,但不会打扰。我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有些声音,一旦听过,就再也无法假装没听见。”
他回复:“欢迎。但请记住,主角不是我。”
雨停后,他抱着女儿站在阳台上。远处天际线染上橙红,城市渐渐苏醒。楼下早餐铺又开始炸油条,锅铲声、吆喝声、电动车启动的嗡鸣,一如那个清晨。
他蹲下身,看着女儿明亮的眼睛,轻声问:“你想不想听听爸爸的新歌?”
她用力点头。
他播放了一段尚未命名的小样:钢琴伴奏下,交织着婴儿啼哭、老人咳嗽、轮椅滚动、风穿过山谷、以及无数普通人说“你好”“再见”“我爱你”的碎片化人声。整首曲子没有主旋律,却有一种奇异的和谐。
“这首歌叫什么?”肖萌问。
“还没想好。”他说,“也许,就叫《我们都曾努力发声》。”
女儿听完,忽然伸出小手,拍了拍音响,咧嘴一笑:“响!响!”
他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任她咯咯笑着踢腿。
他知道,这张专辑终将结束,但这场关于倾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质疑仍在,资本仍在觊觎,流量仍在扭曲真相。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灯、闭眼、静坐,只为听清一段呼吸、一句呢喃、一次艰难的发声。
有人问他:“你觉得《众声》改变了什么吗?”
他在一次访谈中答:“我没想改变什么。我只是想证明??每一个声音,无论多微弱,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就像黑夜里的萤火,单独看不过一星微光,可当它们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整片荒野。”
夜深时,他又一次坐在电脑前,翻看“暗声档案”数据库。新增条目已达两千三百余条:有自闭症少年第一次主动录音说“我想交朋友”;有临终关怀病房里老人用气音说完一生回忆;有战火地区儿童躲在地下室录下的童谣……
他选中一段,标记为“重点留存”,命名为:《人类的声音,从未停止生长》。
然后,他合上电脑,走向卧室。
女儿已在梦中,小脸贴着毛绒熊,呼吸均匀。肖萌侧身躺着,睫毛轻颤,似在做梦。
他轻轻躺下,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这座城市依旧喧嚣,万家灯火如星河倾泻。而他知道,每一盏灯下,都藏着一段等待被听见的故事。
他闭上眼,耳边仿佛响起无数声音??遥远、细碎、执着,像春天解冻的溪流,一寸寸向前奔涌。
只要还有人在听,就不会有真正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