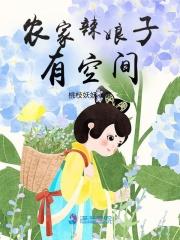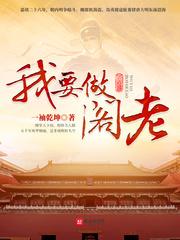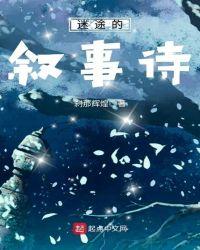笔趣阁>塌房?我拆了你这破娱乐圈 > 第519章 你看懂了吗你就点头(第2页)
第519章 你看懂了吗你就点头(第2页)
“明天去青海吧。”他说,“扎西说他想录一首新歌,用溪水、石头和风。”
苏黎点头:“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
七天后,昆仑山脚下的牧区小学操场上,孩子们围成一圈,手拉着手。扎西坐在轮椅上,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他看不见,但能感知阳光的方向,也能听懂每一种自然的声响。
“这是爸爸以前教我的调子。”他用手语告诉翻译老师,“我想把它唱给山听。”
周南蹲在他身边,打开录音设备。风掠过山谷,带来融雪的气息。扎西开始哼唱,声音稚嫩却不怯懦,旋律简单得近乎原始,像是大地本身在低语。
苏黎悄悄架起摄像机,镜头缓缓扫过每一个孩子的脸??有的戴着助听器,有的肢体残疾,有的因早年高烧导致智力发育迟缓。但他们都在笑,都在跟着节奏拍手。
当歌声结束,周南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扎西想了想,说:“叫《光来找我了》。”
全场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晚,他们在帐篷里整理素材。篝火噼啪作响,远处传来狼嚎般的风声。苏黎翻看着几天来的影像,忽然停下。
“这段能放进纪录片吗?”她问。
画面中,周南正帮一个听障女孩调整耳蜗设备,动作温柔得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艺术品。女孩忽然伸手摸他的脸,然后比划:“你的声音,暖。”
周南愣住,随即笑了:“因为我用心说了话。”
苏黎看着回放,轻声说:“很多人以为纪录片就是要揭露伤痛,可你让我看到的是??即使在最深的困境里,人依然可以活得有尊严、有温度、有希望。”
周南望向星空,良久才开口:“我们总在寻找宏大的意义,其实真正的力量,藏在这些微小的连接里。一句手语,一次触摸,一段被认真对待的声音……它们才是撑住生命的绳索。”
---
一个月后,《众声》全球巡展首站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开幕。展厅中央是一条长达百米的“声音长廊”,参观者戴上特制耳机,走过不同区域,便会听到对应地域的生命之声:广州老城区清晨卖肠粉的吆喝、新疆沙漠边缘孩子追逐骆驼的笑声、挪威极光下老人用萨米语吟唱的古老歌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致辞时说:“这不是一场展览,而是一次集体觉醒??我们终于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与服饰,更体现在每个人独特的发声方式。”
媒体蜂拥而至,追问周南是否考虑商业化运作,甚至有人提议将《众声》做成NFT拍卖。
他在记者会上只说了一句:“如果一段母亲临终前的告别可以标价出售,那人类离野蛮就不远了。”
舆论哗然,争议四起。资本迅速退场,但也有一群年轻人自发组建“声音守护志愿者联盟”,在全国各地开展“闭眼聆听日”活动。学校开始引入《众声》作为心理教育素材;医院增设“声音记忆档案室”,允许患者家属留存亲人最后的话语。
与此同时,林晚带来一个消息:国内某头部综艺平台愿意出资两亿,邀请周南担任一档音乐真人秀的导师,条件是全程跟拍,并允许节目组使用《众声》部分内容进行改编。
“他们想把它变成一档‘感动中国式’的情感秀。”林晚皱眉,“煽情、催泪、热搜导向。”
周南冷笑:“那就等于杀了它。”
但他转念一想,又说:“除非……我们反过来利用这个平台。”
众人愕然。
他解释:“让他们拍,但必须遵守三条规则:第一,所有选手必须包含至少一名残障人士或边缘群体成员;第二,每期节目结束后,开放十分钟‘无声时段’,观众必须闭眼静坐,仅靠耳机收听一段真实录音;第三,最终冠军不颁发奖金,而是资助其完成一项社会声音采集项目。”
林晚震惊:“他们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