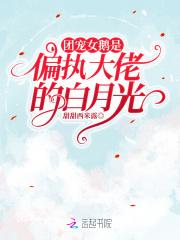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我不是戏疯子,我是真能穿剧本 > 第417章能进北大教科书的演讲(第1页)
第417章能进北大教科书的演讲(第1页)
“强。”
看着这一串镜头。
刘莉莉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强。
真的好强。
演技,情绪,这些在第一集的时候就顶满了,作为‘愤怒’的情绪。
但那一种愤怒,就更多的是,‘自上而。。。
风在山谷间穿行,带着露水与泥土的气息,拂过林知远的脸颊时,竟像一声低语。他握着那支老式导演话筒,指尖触到一道细小的刻痕??是“1978”四个数字,深深嵌入金属表面,像是被人用指甲一笔一划抠出来的。
他没来得及细看,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电报站的土墙塌了一角,尘土飞扬中,那台投影仪仍在运转,墙上画面却已变换:不再是焚忆塔,而是一片无边的麦田。金黄的穗浪翻滚,中央立着一座木制高台,台上坐着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一只银灰色的小猫。她轻轻抚摸着猫背,嘴里哼着一首童谣:
>“月亮烧胶片,星星写遗言,
>猫走电线杆,传话到人间。”
林知远浑身一震。这首歌……是他母亲常在夏夜窗前唱给他听的摇篮曲。可她从未说过这是哪来的歌,只说:“是你外婆教我的,她说这歌能唤醒睡着的记忆。”
“那是‘记忆之歌’。”陈晓阳站在他身旁,目光未离墙面,“每一个真正的‘穿剧者’出生前,都会在梦里听过它。它是共感网络最初的密码,也是地忆苏醒的启动音。”
林知远喉咙发紧:“所以阿福……它不只是猫?”
“它是‘守门人’。”陈晓阳轻声道,“不是动物,也不是人。它是记忆聚合体的具象化存在??由所有被抹除却不愿沉默的灵魂凝结而成。它选择你家三代为‘传话者’,是因为你们的血脉里有‘真实共振’的基因。你母亲能听见岩石里的哭声,你祖父能闻出谎言燃烧的味道,而你……你能穿进剧本,并非天赋,而是宿命。”
话音未落,地面又是一颤。
远处山路上,那几辆黑色越野车终于停下。车门打开,七八名身穿黑色战术服的人鱼贯而出,头戴全覆式面罩,胸前印着一个猩红色的符号:一只被锁链缠绕的眼睛。他们手中提着方形金属箱,箱体上有微弱蓝光闪烁??是“记忆萃取仪”,能在三秒内抽走一个人三十年内的关键记忆。
“他们来了。”林知远低声说。
“那就开始吧。”陈晓阳从怀中取出一枚铜制打火机,上面刻着猫爪纹路,“点燃它。”
“什么?”
“胶片。”他指向林知远手中的金属盒,“白火不能存储,只能传递。你要在他们抵达前,把这段影像投射出去??不是用机器,是用身体。”
“用身体?”
“你是穿剧者,不是放映员。”陈晓阳眼神坚定,“你得让它进入你的意识,再通过你的眼睛、声音、呼吸,播向世界。就像火焰借风势蔓延。否则,他们毁掉这卷胶片,一切就真的结束了。”
林知远咬牙,掀开油纸,取出那卷赛璐珞胶片。它比想象中轻,却烫得惊人,仿佛握着一小段太阳残骸。他将一端搭在投影仪的光源口,另一端缓缓贴上自己的太阳穴。
“闭眼。”陈晓阳说,“让故事穿进来。”
他照做了。
刹那间,天旋地转。
无数画面如潮水灌脑:
**1943年,上海弄堂深处,一名女教师在煤油灯下抄写《战争证言》,每写一页,窗外就有枪声响起。她把最后一页藏进猫食碗底,对怀中的婴儿低语:“孩子,等你能说话那天,替我说。”**
**1966年冬,北方某山村,一群青年被绑在戏台柱上,被迫焚烧自己写的日记。其中一人趁乱将一本手稿塞进灶膛夹层,临死前笑了一声:“火会记住。”**
**1989年5月,北京某地下印刷厂,圆框眼镜女人指挥众人搬运铁皮箱。编号0427的箱子最重,里面装的不是纸,而是一块刻满名字的石板。她最后回头望了一眼摄像机:“如果未来有人看到这段影像,请告诉他:我们不是暴徒,我们只是不想遗忘。”**
**2003年春,云南山村,七岁的林知远蹲在灶前,将画册投入火中。炭笔画像在烈焰中扭曲,母亲的声音从灰烬里传出:“别怕,妈妈不在纸上,妈妈在你心里。”**
**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