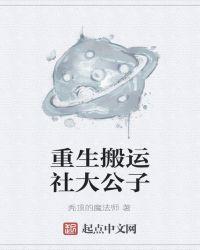笔趣阁>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二十五章 冬至家宴(第2页)
第三百二十五章 冬至家宴(第2页)
蒙恬未擅自答应,而是将使者送往敦煌,请刘肥定夺。
刘肥接见使者时,神情平静:“你主既愿归附,本使自当代为奏请。但我有一问:若他日匈奴大军压境,你们是开门迎敌,还是闭城拒叛?”
使者叩首答:“誓死守城,绝不通敌!若有违此誓,天雷击顶,子孙灭绝!”
刘肥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可以代奏朝廷,准其内附。但条件有三:其一,拆除所有旧有堡垒,改筑秦式城墙;其二,境内通行秦币,废除部落私刑;其三,每年选派十名贵族子弟入敦煌译学馆学习五年以上,期满方可继承爵位。”
使者一一应承。刘肥遂命文书拟就盟约,加盖都护印信,并派快马送往咸阳备案。
此事震动西域。鄯善、龟兹、焉耆等国纷纷遣使打探消息,有的试探性请求通商,有的暗中商议联姻。一时间,敦煌成了整个西域的政治中心,每日进出的使节、商旅络绎不绝,城中客栈爆满,市集繁华胜过关中。
就在各方势力博弈之际,宁远公主的车队终于从咸阳出发。
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前后绵延十余里。除了公主銮驾外,还配有护卫骑兵两千、随嫁宫女三百、工匠五百,以及整整一百辆辎重车??车上装载着书籍、乐器、织机、药材、种子、铜鼎、玉璧,甚至还有专为西域儿童准备的识字板和算筹。
皇帝亲送至灞桥,执手叮嘱:“此去万里,风沙险恶。然你肩负的,不只是婚姻,更是天下太平之望。你要让他们看到,华夏女子不只是柔弱之美,更有刚毅之德。”
公主含泪受命,转身登车。车轮启动那一刻,长安城万人空巷,百姓焚香祷祝,祈愿丝路永宁。
车队一路西行,沿途郡县无不隆重接待。每当进入新城镇,当地百姓都会夹道欢迎,献花敬酒。尤其是那些新建的屯田村,村民们扶老携幼前来观礼,眼中充满敬畏与期待。
一位老农颤巍巍地捧出一碗清水,递给随行的宦官:“这是我们渠里流的第一瓢活水,请公主喝一口,保佑她一路平安。”
那水清澈甘甜,映着蓝天白云,也映着无数普通人对和平的渴望。
与此同时,刘肥已在敦煌主持最后的筹备工作。他下令全城粉刷墙壁,栽种桃李,修复道路,并组织数千民夫在城南修建一座临时行宫,专供公主暂居。他还亲自审定了迎亲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从鼓乐编排到礼宾顺序,从服饰规制到宴席菜单,无不力求庄重而不奢华,威仪而不张扬。
“这不是一场婚礼,”他对属下说,“这是一次国家宣言。我们要告诉所有人:大秦不仅强大,而且文明;不仅征服,而且包容。”
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春日清晨,?望塔上的戍卒高喊:“东方烟尘起!迎亲队伍距阳关不足五十里!”
全城沸腾。百姓穿上节日盛装,手持彩旗与鲜花,涌向城门。译学馆的学生们列队诵读《诗经?关雎》,声音清越悠扬。连那些平日桀骜不驯的胡商,也都换上整洁衣袍,静候盛典来临。
当宁远公主的车驾缓缓驶入敦煌城时,阳光正好洒落在她凤冠之上,折射出七彩光芒。她掀开车帘,望着这座陌生却又亲切的城市,望着街道两旁欢呼的人群,望着远处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忽然落下泪来。
她从未想过,自己的命运会与这片土地如此紧密相连。
刘肥策马上前,单膝跪地,双手奉上象征西域都护权威的金印:“臣刘肥,恭迎宁远公主驾临敦煌。自此之后,西域安宁,万民仰德。”
公主轻轻点头,声音温柔却坚定:“请起。从今往后,我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整个大秦的精神而来。这里,就是我的家。”
那一刻,钟鼓齐鸣,万民同庆。
而在千里之外的咸阳,皇帝再次登上章台宫高台。他手中拿着最新的边报,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萧何站在身旁,轻声道:“陛下,您看,连风都变了方向。”
的确,春风已越过陇山,穿过河西走廊,吹进了天山南北。它拂过新开的学堂,吹动少女手中的书页,卷起商人背包里的契约文书,也将“大秦西境”四个大字,深深地刻进了历史的岩层之中。
没有人再怀疑这条路能否走下去。
因为已经有太多人,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它的长度;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它的土壤;用自己的信念点亮过它的星空。
真正的帝国,不在疆域之广,而在人心之深。
刘肥站在城楼上,目送迎亲队伍远去。夕阳余晖洒在他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如同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他知道,风暴仍会再来,阴谋不会终结,沙漠依旧残酷,人性总有反复。
但他也相信,只要还有人在教孩子写字,还有人在修渠种田,还有人在秉公断案,还有人在仰望北斗星寻找方向??那么,秦人的悠闲生活,就不会结束。
这不是逃避,而是坚守;不是懒散,而是从容;不是停歇,而是积蓄。
他转身走下城楼,脚步稳健。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