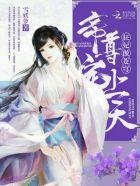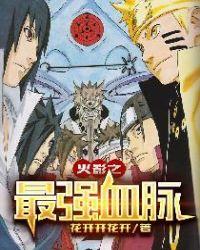笔趣阁>有诡 > 393逊皇帝11(第2页)
393逊皇帝11(第2页)
于是,二人决定亲自出行。临行前,他们在桃屋设下长明阵法,以七枚桃核镇守四方,确保《契录》与忆泉核心不致失控。孩子们被托付给留守长老照料,记学堂暂停授课,唯留一盏灯日夜燃烧,象征归途不灭。
出发那日,春尽夏初,桃实初结。
林照背着药箱与《契录》副本,闻忆手持忆泉玉佩与引归灯残芯,踏上了通往西漠的荒途。沿途所见,皆显异状:村庄废弃,门楣上族姓被刻意刮去;市集冷清,无人谈论祖先;更有甚者,孩童竟不知父母婚配之年,老人忘记亡妻埋骨之所。
“它不止在毁书。”闻忆望着一座空荡书院说道,“它在让人习惯遗忘。”
终于抵达西漠边缘时,已是月圆之夜。残阳如血,映照在干涸河床上,宛如一条凝固的记忆之河。根据最后信号,阿岩被困于“千佛窟”深处,那里曾是西域佛法东传的第一站,如今只剩断壁残垣。
夜半潜入,洞窟内阴风阵阵。墙壁上的佛陀面容已被风沙磨平,仅余轮廓。林照举灯前行,忽觉脚下踩到一块松动石板。掀开一看,竟是一个密格,内藏一卷羊皮卷轴。
展开细看,竟是百年前一位僧人所绘的《共忆图志》,描绘了当时各地保存记忆的方式:北村守灯、南岭修谱、东河说书、西漠绘壁、中州铸钟、东海刻贝、极北刻竹……七法并列,共护人间不忘。
更惊人的是,图志末尾标注:“七法若断其三,则忆泉衰;断其五,则断缘复生;尽毁,则天地失序,众生沦为无名游魂。”
“原来如此……”林照恍然,“它不是随机攻击,是在精准切断七种记忆传承方式!”
正说着,前方甬道忽然亮起幽蓝光芒。闻忆脸色一变:“那是忆泉反噬现象??有人强行唤醒被封印的记忆,却被记忆吞噬!”
两人疾奔而去,终于在最深处见到阿岩。他盘坐于地,双手紧握一块壁画碎片,额头渗血,双眼翻白,口中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我不是我……我不是我……”
闻忆立刻施术,以忆泉之力构筑屏障,隔绝外界干扰。林照则翻开《契录》,找到对应章节,低声诵读稳定神魂的安忆咒。良久,阿岩才缓缓睁眼,第一句话便是:“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自愿删去自己的名字,只为换取一日太平。他们说:‘只要不记得,痛苦就不存在。’”
林照心中剧震。这不仅是断缘的蛊惑,更是一种集体的自我欺骗??人们主动选择了遗忘。
“但我们不能跟着错。”他扶起阿岩,坚定道,“你带回的歌谣呢?”
“在我脑子里。”阿岩苦笑,“纸没了,但我还记得。每一句,每一个音。”
当晚,三人围坐在篝火旁,阿岩开始吟唱。那是一首古老的维吾尔语民谣,讲述一位母亲跨越沙漠寻找失散儿子的故事。歌声苍凉悠远,随着旋律起伏,洞窟墙壁竟隐隐浮现出原本消失的画面:驼队、绿洲、星空、泪痕……
“记忆不怕丢失,”闻忆轻声说,“只怕没人愿意再提起。”
离开西漠前,林照将《共忆图志》拓印三份,一份藏于桃屋密室,一份交予阿岩带回北村重建记学堂课程,最后一份则派人送往极北盲儒处,请他刻入竹简流传后世。
归途中,他们陆续收到其他执灯使的消息:
苏禾成功录下老渔夫口述的《亡亲录》全文,并在当地建起一座“声音碑林”,将所有口传故事录于陶埙之中,风吹即鸣;
北原的赵娘子在冰湖底发现一座沉没的祭坛,坛中供奉着七十二个无名木牌,正是百年前战乱中失踪的孤儿寡母。她将名单誊抄带回,引发周边九村联合追思;
就连最遥远的东海渔村,也有渔民送来贝壳串成的“海语链”,上面刻满祖辈传下的航海谚语与家族誓词,险些被潮水卷走。
七灯渐明,断缘的攻势虽猛,却未能彻底扑灭火种。
回到北村那日,恰逢清明。
桃林花开正盛,守心碑前香火不绝。孩子们围着新立的“忆亭”奔跑,亭中书架已摆满各地寄来的手稿与实物。一位小女孩踮脚取下一册《陈塘家忆录》,翻开第一页,念道:“我的曾祖父叫李承志,他在瘟疫中最先冲进病屋救人……”
林照站在远处听着,眼角湿润。
当晚,他与闻忆再次来到桃林中央。那棵寄居姐姐魂魄的老桃树微微发光,树影中似有人轻轻点头。
林照跪地叩首:“姐姐,七灯已燃六盏,只剩最后一处未通。我们会走下去,直到天下再无人因被忘记而哭泣。”
话音落下,一阵清风拂过,檐下铜铃轻响,竹笛呜咽,似有回应。
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山古庙中,一名年轻道士正对着一本即将焚毁的地方志流泪。火焰舔舐书角的瞬间,他忽然听见风中传来一句清晰话语:
“你还记得吗?”
他猛然抬头,喃喃道:“我记得……我是谁的孩子,我娘临死前说的话,我都记得……”
火焰停住了。
仿佛某种力量横跨时空,轻轻吹熄了那一缕毁灭之火。
桃屋之内,《契录》末页的新字悄然变化,墨迹流转,续写道:
>“执灯者无数,归途唯心。
>灯火所至,即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