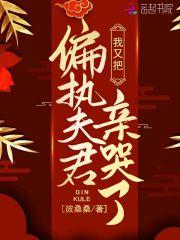笔趣阁>军途:从一封征兵信邮寄开始 > 第三百七十一章 未来战争你是不是讲的太靠前了(第2页)
第三百七十一章 未来战争你是不是讲的太靠前了(第2页)
旅途漫长。火车换汽车,再徒步穿越荒漠边缘。沿途村庄越来越少,风沙越来越大。每当夜宿帐篷,共鸣盒都会自动接收一段微弱信号??依旧是那熟悉的三声铃响,间隔七秒,像是某种导航信标,在荒原上划出一条看不见的路。
第五天傍晚,他们终于抵达新坐标点。眼前是一座被黄沙半掩的废弃气象站,铁门锈蚀断裂,屋顶塌陷一角。但在院子中央,竟立着一口完整的青铜钟,样式与山村小学后山那座极为相似,只是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张秀兰,1953,鸣沙山护林员
>王建国,1967,可可西里科考队员
>李文娟,1981,大兴安岭火灾中逆行救童教师
>陈志强,1995,秦岭隧道塌方前最后一班岗哨
>……
每一行都标注着时间与地点,正是铜柱上记录过的“静默时刻”主角。
“这些人……都是自愿成为锚点的?”小芸低声问。
“不全是。”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三人猛然转身。门口站着一位老人,身穿褪色军大衣,头发花白,面容苍老却不失挺拔。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手指,左耳戴着一枚奇特的骨质耳钉,形状如同螺旋纹路。
“有些是牺牲后被选中,有些是临终前主动接入系统。”他缓缓走近,“我等你们很久了。”
林远喉咙一紧:“爸……”
老人点点头,目光落在小禾手中的陶铃上。“你做得很好。”他对小女孩说,“用等待的节奏唤醒青铜柱,这是连我都没想到的方式。孩子们比大人更懂‘第七时间’的本质??它不属于效率,属于信任。”
他们在气象站地下室找到了新的控制室。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全国地图,七十二个红点闪烁其间,远超原先的七个节点。“这两年,共鸣网络自发扩展了。”老人解释道,“每一份被认真倾听的情绪,都会在地下生成一个新的共振点。现在已经有七十二处‘民间钟楼’在运作,虽然大多数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林远看着地图,忽然发现其中一处红点正在剧烈跳动??正是山村小学所在地。
“怎么了?”他问。
“有人试图切断信号。”老人神色凝重,“来自高层的压力一直存在。有人认为这种‘非标准时间体系’会扰乱社会秩序,削弱执行力。昨天,国防科工局重启审查程序,准备全面回收试点设备。”
“可那些钟……已经长出来了。”小芸低声说,“它们不是机器,是人们愿意停下来的心。”
老人沉默片刻,转身打开一台老旧显示器。屏幕上跳出一段视频画面:一间会议室里,几位官员正激烈争论。一名年轻女研究员站起来发言:“各位,请看这段数据??在过去一年中,实施‘第七时间’的地区,抑郁症发病率下降31%,医患冲突减少45%,交通事故中‘因抢行导致’的比例降低67%。这不是混乱,是另一种秩序。”
镜头切换,出现一张熟悉的脸??竟是当年录制童谣的小学音乐老师,如今已成为心理干预项目负责人。
“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老人轻声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加入这场授时。”
当晚,四人围坐在火炉旁。老人讲述了那段失联岁月:当1998年地核共振失控时,他选择将自身神经节律与主频绑定,以肉身作为缓冲器,防止能量逆冲摧毁全国锚点。结果意识被困在时间褶皱中,既非生,也非死,只能通过极低频波段感知外界变化。
“我听见你们每一次敲钟。”他说,“听见小芸第一次破解共鸣密码时的欢呼,听见小禾在雨夜里自言自语‘我想让世界慢一点’,也听见林远在日记里写‘也许爸爸还在听’。”他顿了顿,“最难熬的是2020年武汉方舱那一夜。那么多人在哭,那么多心跳快要熄灭……我多想告诉他们‘等等,有人在听’,但我发不出声音。”
泪水无声滑落。小禾轻轻举起陶铃,敲了一下。
叮??
七秒后,第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