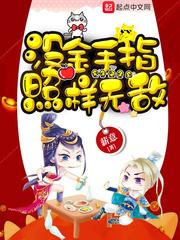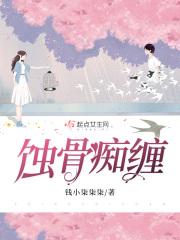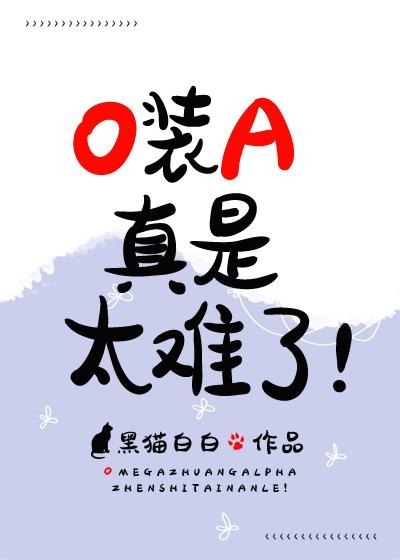笔趣阁>我的低保,每天到账1000万 > 第625章 当老婆的面牵她闺蜜的手(第2页)
第625章 当老婆的面牵她闺蜜的手(第2页)
>明明知道飞不过那个冬天。
>你还把最后一块糖塞给我,说:‘老师别饿着。’
>那一刻,我多想撕掉命运写的剧本……”
歌声未落,整个花园突然剧烈震颤。三百六十五根音波柱同时亮起紫金交错的光芒,增幅阵列发出低沉嗡鸣,仿佛地底有巨兽苏醒。一道光束从中央柱射出,直冲云霄,穿透晨雾,在空中凝成一幅投影??
是一座教室。
黑板上写着日期:1984年3月12日。十几个孩子整齐坐着,有的戴着助听器,有的腿上缠着石膏,还有一个小女孩正用彩色铅笔认真描摹讲台上的男人。
镜头缓缓推进,落在角落的女孩身上。她抬起头,对着空气微笑,嘴唇微动。
林晚听到了。
不是通过耳朵,而是直接出现在意识中的一句话:
“老师,我现在能唱歌了。”
画面消散,光束收回。庭院恢复寂静,唯有吉他余音缭绕。
林晚怔坐良久,才缓缓写下歌名:《你们从来都不是负担》。
他知道,这首歌唱给所有被社会定义为“残缺”的灵魂??那些因病早逝的孩子,因贫辍学的少年,因性别、身份、出身而被迫沉默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中午,他照例去“倾听角”。
推门时,共生藤蔓由蓝转暖橙,表示今日情绪平稳。墙上木牌依旧写着:“这里不说对错,只收真心。”
第一位来访者是个高中生,戴着口罩,声音发抖:“我……我是同性恋。昨天出柜,我爸拿皮带抽我,说我脏。我妈跪着求我‘改回来’。可我真的没得选……我只是喜欢一个人,为什么就成了罪?”
林晚静静听着,递上一杯温水。
“你知道吗?”他说,“二十年前,有个男孩也这样告诉我。他后来跳了江。遗书里只有一句:‘我不是怪物,我只是爱错了时代。’”
少年猛地抬头,眼中含泪。
“但现在不一样了。”林晚轻声道,“你敢说出来,就已经赢了。而且,你不孤单。”
他翻开日记本,写下新篇标题:《被诅咒的爱》。
第二位访客是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她丈夫三年前死于矿难,赔偿金被亲戚卷走,她靠捡废品养活孩子。最近常梦见丈夫站在雪地里,嘴唇发紫,却不肯进门。
“他是不是怨我?”她哭着问,“是不是觉得我没照顾好儿子?”
林晚摇头:“他回来,是因为放心不下。而不是责备。你要替他活着,也要替他爱这个孩子。”
女人抱着婴儿跪下,额头触地。
林晚扶起她,记下故事:《冻在雪里的拥抱》。
一天下来,共二十三人来访。有人讲述被家暴多年终于逃离的妻子,有人忏悔年轻时霸凌同学导致对方自杀;还有一位盲人调音师,说自己每晚都能听见“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音阶”,像是有人在远处弹奏一架永远差半个音的钢琴。
“那是记忆的杂波。”林晚说,“有些人走了,但他们的频率还在震荡。”
傍晚归家,天空再次异变。
这一次,不是光带,也不是裂缝,而是一场无声的雨。
雨滴透明,落地却不湿地面,反而悬浮在半空,每一颗都折射出不同的画面:一个老人在床前念亡妻日记,一对情侣在墓碑前交换戒指,一名战地记者播放录音机里最后一段战友的笑声……
陈默拄拐赶来,脸色激动:“全球共感潮达到峰值!南极共感器同步率突破95%,心塔幼苗已长出第五朵花,持续十七分钟!更重要的是??”他喘了口气,“我们接收到一段反向信号。”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