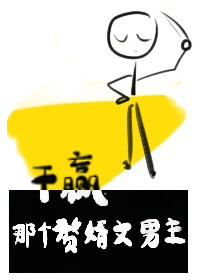笔趣阁>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 > 7080(第9页)
7080(第9页)
至少,秋闱的前两日,他在国子监不就听到师兄们在讨论朝廷征发大军,前往广源州平叛的事了么。路过的两位师兄甚至讨论起了狄青的出身与经历。说明主帅的人选并非秘密,稍加了解就能知道。
而且前一日的经义题,还出现了《公羊传》中“九世之仇犹可报”的题目。而汉武帝就是第一位讨伐南越、经略西南,把后世的云贵纳入中原版图的皇帝。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提醒呢?
再不济对侬智高的叛乱不甚了解,真宗皇帝在位期间推广过占城稻吧。大理更是年年稳定朝贡与大宋,大理的商人亦在汴京的街市上稳稳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说,“大宋如何处理与西南边民的关系”,看似是一道偏门的题目,实则是一道有坡度的选拔题,考的就是考生们日常对国家大事、国计民生、乃至急智变通的考验程度。
果不其然,最初的抓耳挠腮过去后,考场的学子们开始疯狂搜刮脑细胞内的素材。
听说过“占城稻”的,写应当和西北边民处理好关系,从中引入物种。就像当年张骞从西域带回来葡萄、土豆、香菜……等等中原闻所未闻的作物一样。
了解一些侬智高叛乱与狄青平叛内情的呢,则分为了两个方向。第一派的态度较为强硬,说要用武力方能使周遭国家臣服,侬智高叛乱挑衅了大宋的威严,平叛大军只有靠胜利方能震慑一方。还有一派则认为,自古以来华夏正统之国便有“怀柔远人”的传统,要让边民人心归附必须通过教化,让他们食宋之米、识宋之字才行。
至于扶苏呢?
扶苏比较贪心,他都写了。
先是谈及自古以来中央与西南的关系,譬如说赵佗以秦军二十万为基础建立南越国——写到这里扶苏还有点心酸呢。唉,整整二十万的秦国子民呀,也就比他在上州监军时的戍边军少了十万人呢。
他其次列举了一番西南边地的丰富物产:茶叶、滇马、药材、树木……以此论证了大宋与西南边地百姓、诸多小国保持商贸往来的合理性。又举了张骞、真宗皇帝的例子,强调了引入新物种的必要性。可惜棉花的存在暂且需要保密,不然他一定写这个的。
再在此基础上,谈及侬智高其人叛乱的前因后果——大宋的绥靖政策固然被验证是失败的,杀掉侬智高父亲的交趾李氏王朝的嚣张气焰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次大宋的平叛大军,不仅要消灭在宋境内作威作福的侬智高,还要震慑、乃至威胁到交趾李氏王朝,让他们不再敢作威作福哪怕一点。
他代表自己,相信狄青将军一定能做到。
至于最后一点,扶苏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写上了“改土归流”几个字来。阻挠边民的人心向宋的其实并非他们自己,而是当地的土官世家阶级。他们当然希望治下的子民“乃不知有宋”,这与朝廷的期望是背道而驰。所以,要想真正使边民人心归附,改土归流势在必行。
只是当地的土司家族世代相传、实力雄厚,又借助宗教等手段控制着边民们的思想,“改土归流”势必不是一日之功,而是项需要徐徐图之的浩大工程。但正如前文所说,加强与边民们的商贸往来,迟早会让大宋在他们的心中留下印象。而这说不定就是能撬动改土归流的一个支点。
“呼……”
写完最后一个字停笔,扶苏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珠。他想说的话太多,真写下来还真需要一点时间,同时高强度的脑力活动也让他腹中空空。但这次,他可没有首场那么悠闲了,抓了一把馓子塞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飞快地整理起草稿,然后开始誊抄。
他誊得手都酸了,中途不停地抬头看蜡烛,才在考试结束还有一炷香的时间堪堪停笔。同时开始检查起前面的内容来。
没错,之前关于水利的策论题,他还像现代的应用题一样列了算式,给出了堤坝长度的确切数字——就像后世数学里的应用题那样。不过比起什么甲军追乙军,什么一边水管放水另一边水管吐水,大宋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验算了一遍,确定没有算错,又发现没有检查出错别字之后,蜡烛将将燃尽。胥吏们大声喊着“举试结束”,一边冲进了每一个考室中收捡试卷,待这一项完成后,才放行了被困在这小小方寸之间的学子们归家。
人群涌动之间,扶苏就看到了好几张面色灰白、垂头丧气、如丧考妣的脸。没看到晏几道,或许被人群冲散了。但到了考室外与师兄们会合之际,却发现他们的脸色都还不错。
“真是托了你的福啊!赵小郎!”李观澜搓着手,一脸劫后余生的模样说道:“要不是你时不时在我们耳边念叨,什么广源州啊主帅啊,我们哪里会注意到西南那边呢?”
“……我哪有!我也只说过一次!”
扶苏脸色微红,争辩道。
他一直很小心地不在师兄们面前提及太多朝廷大事,要是暴露了自己了解得太多,一不小心掉马了可怎么办?
“好了,既然赵小郎你不愿居功。我来居功总行了罢?”范纯仁眉眼弯弯:“父亲给我的来信中确有言及西南平叛一事。大军的主帅狄将军便是由他引荐的。只是父亲也很奇怪,难道说京中似乎也有人听闻过狄将军的勇武过人,举荐之人列出的条件,仿佛是可着狄将军长的似的。”
“父亲命我在京中打听一下风声,奈何我能力不足,实在没打听出一二来。”
在范纯仁看不见的地方,扶苏心虚地移开了眼睛,像是在心不在焉盯着青空中的飞鸟,实则在心中吐槽:师兄,你当然打听不出来了。那是我和官家的密信,别人能看到才怪了。
不过由此一番话可以听出,至少他的友人们发挥得都不差。至少最后一题都有话可写。又寒暄了一会儿,由苏轼提议道:“我们要不先回国子监吧,有什么话在路上慢慢聊。”
他回望了一眼狭窄的、如蜂窝一般的考房,心有戚戚焉地闻了下袖子:“然后回去仔细沐浴一番,我真是受够了。”
“把身上洗干净之后,再一起去相国寺夜市好好地搓一顿,嘿嘿!”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经过这一次秋闱,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考房会如此臭名昭著。实在是太狭小,太憋闷了。小孩子还好,大人在里面屈腿都困难。更要命的是,倘若这次中举了,明年春天还要来同样的地方再接受一次酷刑。
扶苏幽幽地说道:“那也比没中举,然后不得不每三年自费来这里受刑好。”
“嘶。”苏轼倒吸一口凉气:“你说得对。赵小郎,我明天,哦不今晚就要去相国寺拜拜文曲星君,恳求他保佑我这次能中举。”
“可你已经交卷了。”扶苏发挥了唯物主义者的冷酷作风,无情地拆穿道:“再拜哪一位菩萨都没用了。”
“……那不是还有批卷吗?万一星君保佑我,让批卷的老师看我顺眼了么?”
他们经历完一场大考,心情无比轻松,自在地在回家路上插科打诨。可另一边的阅卷组,已然紧锣密鼓地忙碌了起来。
欧阳修是本次秋闱的主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