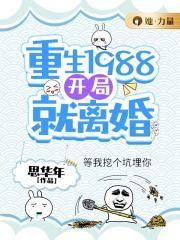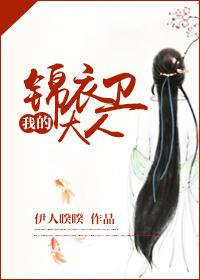笔趣阁>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 > 90100(第14页)
90100(第14页)
所有笼罩在范仲淹脑海中的迷雾,都随着这个猜测迎刃而解。赵小郎今年四岁,宫中那位姓赵的小郎,恰巧也是四岁,而且,是除了官家之外唯一有可能使唤得动皇城司的人选。
他突然福至心灵地问:“你……您让我们父子二人保密,就是为了这个?”
扶苏乌莹莹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区区一个称呼的变化,他就知道,范仲淹肯定是听懂了。
他弯起唇角,轻点了一下头:“晏相公、富相公、欧阳公他们都知道。我独独瞒着您有什么意思?反正您迟早会知道的。”
“……”
范仲淹沉默了。真相带来的后遗症太大,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唯独范纯仁一人在状态外。他看了看扶苏,又看了看扶苏,不知道这初次见面的两人怎么就互相称呼“您”了。还有,他们说的“这件事”又是什么?
范仲淹叹气一声,拍了拍长子的肩膀,干脆把话挑明了说:“纯仁,你也是运气好,竟有一位亲王做师弟。”
范纯仁:“……啊?!”
他原地愣怔了好久,久到扶苏端详着他因失语而震惊的模样都忍不住发出一声笑。恍然回神后,迅速整理了表情,第一句话就是:“我会替你保密的,师弟……成王殿下。”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子固、观澜、苏小郎他们我都不会提……等等,不对,苏小郎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扶苏愈发忍俊不禁。也是没想到啊,几次掉马下来,最有意思的反应居然来自师兄。
他笑过之后,又安慰起略显失望的范纯仁:“他确实知道得比较早。不过不是我说的,是他偶然撞破的。”
“何时?”
“唔,官家来国子监视察的时候吧。”
范纯仁和扶苏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不觉喃喃道:“难怪呢,难怪你敢跟祭酒作保证,官家定会莅临国子监。”
敢情人家是来看自己儿子的。
但扶苏飞快想到了什么,脸色绷住,看起来有些紧张:“师兄,三元之事,实非我所愿。我事先也并不知情。”
“至于那些特殊待遇,完全是官家为了涮我的……”他无奈地说道。
扶苏掉马后最担心之事,一是平白疏远,二是觉得他仰仗身份沽名钓誉。范纯仁乃今科一甲第四,自己可是占了前面的一个名次,他真的很怕范纯仁多想。
范纯仁摸了摸扶苏糯乎乎的小脸蛋:“浑说什么呢。那个位置就该是你的。”
他笑着抬起头:“京中士子无不捧读《捧雪集》、百姓人人传颂、抢着认领棉花。谁还记得,离它面世不足二月?”
“这般手笔,朝中有谁能做到?”
范仲淹也无比赞同地点头:“还有那向北走私棉花的想法,就连我亦想不出来。”
他认可了这个计策的可能性之后,又小心翼翼道:“只是……能不能在惠及北人之前,先让边陲的将士和百姓们有棉衣可穿呢?”
“当然了。”扶苏说。
虽然北边的十六州也是广义上的汉人。但有好东西当然要先紧着自己家。这个道理扶苏当然是懂的。
他掰着指头算起数来:“今年现在汴京城附近推广,待明年把种子全国种遍,不愁边关的将士百姓没棉衣可穿。”
“待到后年,阿菩她们才会出发北上。”扶苏顿了一顿:“到时候,广源州新辟的草场养的西北良驹,第一批也该长大了。”
随着他的话,范仲淹的呼吸都轻了。
他没有问草场和良驹何处而来:“所以,成王殿下,你是要……”
“莫非师父您忘记了,我殿试上写的文章是什么了?”
范仲淹长呼一口气,微微苦笑:“是平戎策。”
“只是,我没想到有生之年就能见到……”
后几个字,他压在了舌尖。“事以密成”的道理谁都懂,正因如此,才不能把关乎国运之事常常挂在嘴边,予人一种大业已成的错觉。
范仲淹无比诚恳地说道:“惟愿来年和后年风调雨顺吧。”
扶苏也点头连连:“是呀是呀。”
没办法,农业国靠天吃饭是这样的。粮食储备充足才有资本打得起大规模战争。倘若哪一年大宋遭了天灾,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只能以年为单位往后推迟。
关于大宋未来的国策,就在一老一少如闲聊般的语气中定了基调。范纯仁在一旁听得流汗不止。这好像不是他一个不入品的新科进士能听的,真的没问题吗?
“对了,您既然回已经到汴京了,何日上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