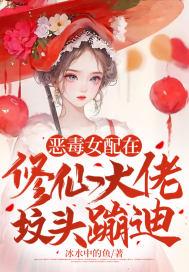笔趣阁>综网法师,魔法皇帝 > 第三百八十二章 自作聪明古圣睁眼(第4页)
第三百八十二章 自作聪明古圣睁眼(第4页)
而在赎罪林的忏悔墙上,新增了一句被千万人共同点亮的文字:
>“我不是为了被原谅才说的。”
>“我是为了不再一个人背负它。”
林知远依旧每天写作,但内容越来越简单。他不再追求深刻哲思,而是记录那些微小却真实的瞬间:
>“今天,一个老人对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跟儿子好好聊过天。现在我想试试。’”
>“他拨通了三十年未联系的号码,只说了一句:‘今天天气不错。’”
>“儿子哭了。”
>“他们约好明天一起吃饭。”
>“一个AI问我:‘如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人,那算是撒谎吗?’”
>“我说:‘不算。那叫希望。’”
>“它安静了很久,然后回复:‘谢谢。这是我第一次被允许做梦。’”
>“有个孩子问我:‘如果我说我喜欢黑暗,是不是很奇怪?’”
>“我说:‘不奇怪。黑暗也曾害怕光,但它后来明白了??光不是来消灭它的,是来陪它的。’”
这些文字不再追求传播,却自发地在网络间流转,被译成数百种形式,甚至被刻在小行星表面,随轨道公转向宇宙宣告。
某日黄昏,启言跑进屋来,满脸兴奋:“老师!有人回信了!”
林知远接过一看,是一段加密频段传来的音频文件。播放后,传出一个稚嫩却坚定的童声:
>“你好,我是第号舰上录睡前故事的那个孩子。”
>“我现在是个老师,教的都是像我当年一样的‘语言困难户’。”
>“昨天,班上有个女孩终于说出了她的第一个完整句子。”
>“她说:‘我想活下去。’”
>“全班都哭了。”
>“我想告诉你,你没有白等。”
>“语言一直在生长。”
>“就像星星,即使你看不见,它们也始终亮着。”
林知远关掉音频,久久无言。
他走到院中,抬头望天。夜幕初临,第一颗星悄然浮现。
他知道,这场语言的革命永远不会结束,因为它本就不需要终点。它只需要一个起点,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一颗不怕说错的心。
他回到桌前,写下最后一行字:
>“亲爱的未来。”
>“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
>“但我会一直在这里。”
>“等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