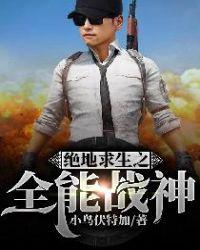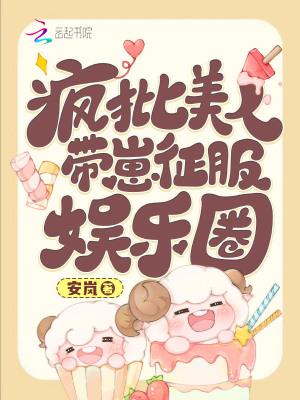笔趣阁>西游:长生仙族从五行山喂猴开始 > 第一百六十章 姜明成婚山中变故(第3页)
第一百六十章 姜明成婚山中变故(第3页)
虽仍不解大儿子近年行事何以透着股急切。
可眼下瞧着这要添丁进口的光景,他那平日沉静如古井的眸子里,终究漾出了一丝压不住的喜色。
山中过日子,没个年头的概念。
檐下青苔一层又一层,院里的老槐树悄悄添了三圈年轮,不知不觉,三年便这么过去了。
祠堂里,香火依旧。
姜明依旧每日雷打不动,盘膝坐在蒲团上,替一家老小讲那些玄虚得能绕三道弯的经义。
嗓音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仿佛永远不急,可身上的气度,早已不同往昔。
三年前,他是口深井,如今,倒像是一潭深水,水面静得出奇,底下却不知藏着多少渊沉。
姜义在下头听着,只觉这大儿子愈发瞧不透了。
竟像与整座祠堂、整片后山的气机拧作了一处,再分不出彼此。
供桌上,姜亮的神魂,经过三年经文日夜的浸润,早不是当初那股飘忽影子。
魂体凝得仿佛带了三分骨肉,伸手去“碰”,竟有若有若无的实体感,只是还禁不得大力。
一上午的讲学罢了,日头正挂在头顶。
一家人说说笑笑回屋吃午饭。
刚一在桌边坐下,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家伙就蹒跚着跑过来,扑在姜明腿上,奶声奶气地喊:
“爹!骑大马!”
姜家对子孙的名字,向来没什么严格的讲究,怎么顺口怎么来。
可姜明还是循着自家小弟的取名路子,给自个儿这个大儿子,取了个单名,叫姜钧。
钧者,千钧也,意味沉得很。
姜明笑着将小家伙一把抱起,放在膝上,一家子围着桌子,其乐融融。
窗外蝉声正盛,院里老槐的影子落在饭桌上,摇得人心里一片安稳。
姜义瞧着这番光景,眼角的笑纹,又深了几分。
午饭过后,院里渐渐静了下来。
姜明却没急着回书房,伸手将姜钧一扛,安在自己肩头,像架小马似的驮着往后山走去。
路过屋后那几株灵果树,他随手摘下几枚红得滴汁的果子,塞进儿子怀里让他抱着。
小家伙笑得直打跌,果汁顺着小手滴落,父子俩的笑声一路被山风带远,不多时便没入林影深处。
姜义端着茶盏,站在院中石阶上,目送那对父子消失在青翠之间,茶香氤氲里,只觉这一幕甚是顺眼。
正此时,村道尽头忽然扬起一条尘龙,一道瘦长的身影自尘雾中疾奔而来,脚步急如鞭响。
姜义眯了眯眼,认出是自家那孙儿姜钦。
这孩子骨格生得好,天分也高,如今将满十三,已长得与成人肩头相差不远。
筋骨打熬得扎实,步伐沉稳里透着股锐气。
平日随姑姑姜曦打理古今帮的事,又与双胞胎妹妹姜锦一同在帮中历练。
仗着自身的手底子,加之大嫂赏的那匣宝箭,他在帮中少年里已是声望颇重。
最喜的是骑马射箭,马蹄一响,箭去如风,真有股江湖游侠的派头。
几日前,他才同姜锦带着帮中一众青壮进了前山深处,猎兽采药,按理此时不该回得这般匆忙。
可眼下,姜钦已冲进了院,一脸通红,额角渗着细汗,气息还未来得及收匀,就急切扑到姜义面前。
“阿爷,不好了!”
那声音带着破音,像被什么劲力催逼出来似的,他喘了口气,又急急道:
“我……我在山里救了个人……是……是那位刘家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