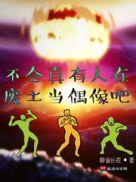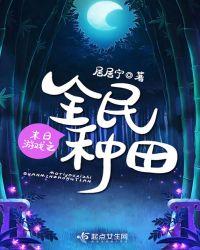笔趣阁>冬日重现 > 第233章 古庙青灯孑然一身四(第1页)
第233章 古庙青灯孑然一身四(第1页)
张述桐盯着那条青色的蛇,回忆起脸边冰冷滑腻的触感,只见青蛇爬上路青怜的胳膊,却没有如他想象般停留在那里,路青怜接着微微弯腰,青蛇又顺着她的手臂爬回了地面。
做完这一切,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
录音机沉默着,屏幕漆黑如墨,仿佛耗尽了最后一丝余温。林昭将它贴近胸口,试图用体温唤醒那沉睡的电路。风从灯塔破败的窗框灌入,卷起地面积雪,在空中划出细碎的螺旋。他闭上眼,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膜中回响??一下、两下……缓慢而坚定。
忽然,一丝微弱的震动自录音机深处传来。
像是某种沉眠的神经被轻轻拨动。
屏幕上浮现出一行极淡的文字,如同雾气凝成:
>“去听井底的声音。”
林昭猛地睁眼。青石村?那口干涸十年的老井,此刻竟渗出了水?还浮着桃花瓣?他翻出背包里的地图,指尖沿着山脊线向南滑动,最终停在一个几乎被墨迹覆盖的小点上:**青石村,北纬31°28′,东经115°07′**。那里曾是“桃源计划”的第一个试点村落,也是小芽最初苏醒的地方。
他没有犹豫。
当天下午便启程下山。暴风雪稍歇,但积雪仍深及膝盖。他靠着指南针和残存的卫星信号,在荒无人烟的峡谷间跋涉。途中遇见一群迁徙的岩羊,领头的母羊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他很久,然后缓缓低头,用角推开覆雪,露出一块半埋的石碑。上面刻着模糊字迹:
>“信若不灭,井终会醒。”
林昭跪下来,用手拂去冰碴,发现碑后竟插着一只褪色的红风筝,线轴早已断裂,只剩几缕麻绳缠绕在石缝之间。他认得这只风筝??是浪小时候画的那只,船形,尾部缀着蓝布条。他曾说要让它飞到海那边去,捎句话给阿宁。
“你还记得他。”林昭轻声说,不知是对羊群,还是对这片土地。
第三日黄昏,他终于抵达青石村。
村庄静得出奇。屋舍大多坍塌,木门歪斜挂在hinges上,墙上爬满冻死的藤蔓。唯有村中央那口老井周围寸草不生,地面干燥得反常,仿佛有股无形热量持续蒸腾。井沿由青石垒成,边缘磨损严重,布满深深浅浅的绳痕。林昭俯身望去,黑洞洞的井底已不再干涸,一汪清水静静荡漾,映不出星光,却泛着淡淡的粉晕。
他取出录音机,低声问:“能听见吗?”
水面微微一颤。
随即,一圈涟漪自中心扩散,水中倒影开始扭曲变形。原本应是天空与枯树的画面,渐渐化作一间教室??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黑板上写着“冬令节联欢会节目单”,底下有一行稚嫩笔迹:“表演:纸船漂流记(主讲人:小芽)”。
画面流转,一个瘦小的女孩站上讲台,辫子扎得歪歪扭扭,手里捧着一只手工折成的纸船。她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
>“老师说,人死了就会变成星星。可我不信。我觉得,如果没人记得你,连星星都不会为你亮。所以我每天折一只纸船,放进井里,希望它们能漂到大海,找到那些走丢的记忆……今天是我第一百天投递,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愿意帮我一起寄信吗?”
全班寂静片刻,然后一个男孩举手:“我愿意。”
又一个女孩:“我也愿意。”
越来越多的手举起,最后整个教室响起齐声应答:“我们愿意!”
影像戛然而止。
水波恢复平静,倒影重回夜空。但这一次,林昭清楚看见,水面上浮现出新的字迹,一笔一划由花瓣拼成:
>“请替我把第一百零一封信送出去。”
他心头一震。
立刻从背包中取出备用纸张,摊开在井边石台上。握笔时手指僵硬,但他强迫自己写下第一行:
>“亲爱的未知收信人:
>我是林昭,代小芽执笔。她没能写完的最后一封信,由我来完成。”
笔尖沙沙作响,思绪如潮涌来。他写下小芽如何在广播站偷偷接入民用频道,如何用桃树花粉激活沉睡的音频记忆体;写下她如何教会孩子们折纸船,每只船里藏一段录音,投入村中七十二口古井,借地下水脉形成天然共振网络;更写下她在系统围剿前夜,将自己的意识拆解成三千段碎片,分别封存在不同媒介之中??一幅蜡笔画、一瓶井水、一片落叶、一声咳嗽……
“她说,只要有人愿意继续写信,她的故事就不会结束。”
写到这里,泪水滴落在纸上,晕开墨迹。林昭没有擦拭,任其流淌,像一场迟来的雨。
他将信折成纸船模样,轻轻放入井中。
船未下沉,反而悬浮于水面,缓缓旋转。刹那间,整口井亮了起来,幽光自水底升起,顺着井壁攀爬,照亮四周废墟。那些倒塌的屋檐下,竟纷纷浮现投影??全是村民昔日生活的片段:母亲哄婴孩入睡、老人晒太阳打盹、孩童追逐野猫……每一幕都带着温暖的噪点,宛如老式胶片放映。
而最清晰的一幕,出现在村祠堂遗址上方:
小芽站在人群中央,身穿洗旧的校服,手里拿着一朵塑料桃花。她抬头望天,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