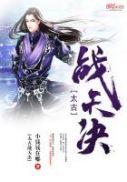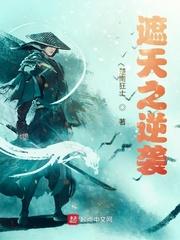笔趣阁>快婿 > 370专业攻城上(第2页)
370专业攻城上(第2页)
“你做得很好。”他递给她一份文书,“这是新拟定的《边军律令》,从今日起,西北五州境内,军令高于王法。赋税、刑狱、征役,皆由我军统辖。”
她接过文书,指尖微颤:“大帅,这等同于……自治。”
“不错。”他直视她,“朝廷既然不愿给我们活路,那就别怪我们自己打出一条生路。钟剑屏,你愿意跟我走到最后吗?”
她抬头,望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那里有野心,有决绝,也有对她从未掩饰的信任。
“属下追随大帅,生死无悔。”她单膝跪地,声音坚定。
赵立宽扶起她,轻声道:“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要交给你一件更重要的事。”
他从案下取出一枚青铜虎符,一半刻“镇西”,一半刻“宁英”??那是先帝御赐、象征边军最高调兵权的信物。
“这一半,归你执掌。”他将半符放入她手中,“从今往后,你不仅是我的副手,更是西北军的监军。若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意图背叛大周社稷,你有权持符斩之。”
钟剑屏浑身一震,几乎握不住那枚冰冷的虎符。
“大帅!这……这不合祖制!”
“祖制?”赵立宽冷笑,“祖制能让百姓吃饱饭吗?能让将士不死于冻饿吗?钟剑屏,我不是要造反,我是要救这天下于腐朽之中。而你,必须成为那把悬在我头顶的剑。”
她久久不能言语,最终深深叩首:“末将领命。”
数日后,朝廷再度派使臣前来,宣读圣旨:嘉奖赵立宽安抚外夷之功,赐锦缎千匹,黄金百斤,并命其择日返京述职。
赵立宽接旨时面带微笑,设宴款待使臣。席间谈笑风生,称颂天子圣明。可当夜,他便召集心腹将领,下达密令:“即日起,全军进入战备状态。修缮烽燧,加固城防,囤积火油滚木。另,派遣死士潜入长安,监视三省六部动静。”
钟剑屏奉命接管情报网。她将原属皇室耳目的细作逐一排查,或收买,或铲除,重建属于西北军的暗线系统。她在长安布下七处密站,分别联络吴光启、礼部郎中李崇义、禁军校尉秦越等人,确保朝中一举一动,三日内必达西北。
一个月后,急报传来:北狄可汗亲率十万骑兵南下,已破长城隘口三处,幽州告急!
朝廷连发八百里加急,召各路节度使勤王。诏书中特别点名:“镇西大将军赵立宽,素有忠勇,宜速引兵东援。”
幕府议事厅内,诸将争论不休。
“大帅,此乃立功良机!若能解幽州之围,便是救驾之臣,朝廷再难打压!”
“不可!”另一将反对,“我军根基尚浅,长途奔袭风险极大。且北狄狡诈,恐是诱敌之计。”
赵立宽沉默良久,忽然问钟剑屏:“你怎么看?”
她起身,指向舆图:“北狄南侵,确有其事。但我怀疑,背后有人推动。”
“谁?”
“皇后。”她声音清冷,“她知您兵强马壮,迟早成患。与其等您壮大,不如借北狄之手消耗我军。若您不去,便是抗旨不忠;若您去,便可能陷入重围,损兵折将。”
帐内一片哗然。
赵立宽眼中寒光一闪:“所以,她是想逼我两难?”
“正是。”钟剑屏道,“但她忘了,您早已不必听命于诏书。”
赵立宽缓缓起身,走到窗前。远处,新建成的炼铁坊正冒着浓烟,工匠们昼夜不息,打造兵器铠甲;屯田区麦浪翻滚,百姓安居乐业;市易司商旅络绎,金银充盈库房。
他回头,一字一句道:“传令??全军不动。”
众将惊愕。
“就说‘粮草未备,道路阻塞,暂缓出兵’。另,修表一封,言辞恳切,痛陈苦衷,请求宽限一月。”
“可……若朝廷降罪?”
“罪?”赵立宽冷笑,“他们敢动我,就得准备好面对一支不受控制的边军。钟剑屏,你立刻拟一道檄文,不提反叛,只说‘为民请命,为国守疆,虽死不避’。抄送各州刺史,传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