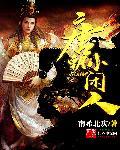笔趣阁>给,主说这个好使 > 71 世界很大(第2页)
71 世界很大(第2页)
白猫缓缓站起,走向一块裸露的红色岩石。它抬起前爪,轻轻按在石面。刹那间,整块岩石变得透明,内部显现出密密麻麻的微型人影??全是死于非命却未曾安息的灵魂,他们嘴唇开合,却无声无息。
“它们需要一个喉咙。”玛鲁卡说,“一个能替它们说话的存在。”
苏晓明白了。林远完成了对地球的倾听,而现在,人类内部那些被压抑、被忽视、被抹除的声音,也需要一次彻底的释放。否则,共感网络只能停留在表层共鸣,永远无法触及真正的疗愈。
“怎么做?”她问。
“仪式必须在‘血月之夜’举行。”玛鲁卡望向天空,“月亮即将进入地球阴影,届时天地之间的屏障最薄。我们将开启‘逆听之门’??不是我们去听世界,而是让世界来听我们。”
准备工作持续了七天。蒙古教师用孩子们的手印绘制共鸣符文;巴西少年从亚马逊带来会唱歌的藤蔓,缠绕成环形祭坛;苏晓则取出林远留下的日记残页,将其焚化后混入黏土,塑造成一颗空心陶球,象征“容纳万千声音的容器”。
血月如期而至。
当月全食开始的瞬间,玛鲁卡开始吟唱。她的声音极低,几乎低于人类听觉阈值,但每一声都引发大地震颤。白猫跃上陶球顶端,发出第一声叫唤??那不是喵呜,而是一段复杂的情绪编码,包含痛苦、遗憾、宽恕与渴望。
随着吟唱深入,地下传来回应。
先是细微的滴水声,接着是金属摩擦般的嘶鸣,最后汇聚成一股浑厚的低频嗡鸣,仿佛整个星球都在调整耳膜。
陶球裂开了。
从中升起一团流动的光影,形态不断变化:时而如孩童蜷缩,时而如战士持剑,时而如母亲哺乳,时而如老人垂死。每一个形态出现,都会伴随一段声音爆发??
“我不是懦夫!我只是怕伤到你!”
“我知道错了,可我已经没机会道歉了!”
“为什么没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出生?”
“我恨你,但我更怕失去你。”
这些声音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千百年来被压抑的集体潜意识喷发。它们冲向夜空,在血月周围形成一圈螺旋声环,继而折射回地面,灌入每一位参与者耳中。
苏晓跪倒在地,泪水滑落唇边。她听见了五岁时衣柜里的自己,听见了广岛母亲抱着焦黑婴儿的哭喊,听见了战壕中士兵写完遗书后的最后一口气息……她想要捂住耳朵,却发现双手早已化作半透明,内部流淌着与林远消散时相同的光丝。
“我也要成为容器吗?”她颤抖着问。
玛鲁卡握住她的手:“不是‘要’,是‘已是’。你早就开始了。每一次你替别人流泪,每一次你为陌生人的痛苦停下脚步,你的身体就在为这一刻准备。林远走了,但桥梁不能断。总得有人继续站着,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开口。”
苏晓仰望血月,深吸一口气。
她张开嘴,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不属于她的旋律??那是三十年前一场校园枪击案中,一名高中生临终前在心里哼唱的童谣;紧接着,又变成十九世纪非洲奴隶船上,母亲低声哄睡孩子的摇篮曲;再后来,是未来某位宇航员在太空站崩溃时的呓语:“我想回家……哪怕地球已经不在了……”
她的声带不再属于她。
她的喉咙成了通道。
她的存在,成了亿万沉默者的扩音器。
这一夜,全球共有十七万人在同一时刻惊醒,耳边回荡着完全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嗓音。他们不知道是谁在说,也不知道说了什么,但他们全都哭了,仿佛终于听见了自己一生都在等待的那一句:“我在这里。”
仪式结束时,白猫倒在陶球旁,气息微弱。它的毛色逐渐褪成灰烬色,身体变得轻盈如尘。玛鲁卡将它抱起,轻声道:“谢谢你,把它们都送回来了。”
猫最后看了苏晓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熟悉的金色光芒??那一瞬,她分明看到了林远的笑容。
第二天清晨,澳洲红土中心的地表出现了一个新湖泊,湖水漆黑如墨,却倒映出整个银河。当地人称它为“言渊”,传说只要对着湖面说出真心话,湖底就会升起一朵发光水莲,承载着话语沉入地心。
而苏晓回到“聆寂林”后,发现林冠间多了一条常年不散的雾带,形状宛如人耳轮廓。每当有人走入林中倾诉心事,雾气便会轻轻包裹对方,随后沿着树根流向远方。
十年后,联合国正式解散“共感事务特别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倾听理事会”,总部就建在“聆寂林”边缘。理事会不做决策,只负责收集、整理、传播世界各地的“未言之声”。每年春分,人们会在林中点燃无焰烛火,纪念所有为倾听付出代价的生命。
苏晓活到了九十三岁。
临终那日,她独自走进森林最深处,坐在当年林远消失的位置。她感到身体越来越轻,皮肤下浮现出细密的金黑纹路,与十年前如出一辙。
她笑了。
“轮到我了。”她说。
风吹过,树叶沙响。
一颗露珠从叶尖坠落,砸进泥土的瞬间,仿佛有谁轻轻应了一声: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