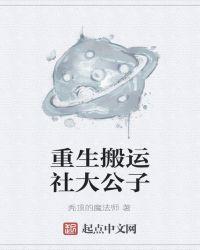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第一国舅 > 第653章 存在感(第2页)
第653章 存在感(第2页)
一字一句,如金石落地,回荡在殿宇之间。群臣俯首聆听,连几位年迈老臣也挺直脊背,神色凛然。讲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时,马寻忽然抬眼,扫视全场,朗声道:
“今有宵小妄图以妖言惑众,污我储君之心,乱我社稷之基。然天理昭昭,岂容邪祟横行?吾辈读书人,当以正压邪,以诚破妄!若有不轨之徒,藏形匿影,终将如鼠窃狗偷,难逃天网!”
此言一出,满殿皆惊。许多人互相对视,已听出其中警告之意。朱标坐在御座旁,微微颔首,眼中闪过赞许。
讲会毕,百官退去。马寻并未离开,而是召来锦衣卫指挥使蒋?,低声吩咐:“陈氏已招供,供出另有同党藏身于净乐堂??那是供奉先帝嫔妃养老之所。你即刻带人前往,务必活捉主谋。”
蒋?领命而去。半个时辰后,捷报传来:在净乐堂偏殿密室中,搜出大量符咒、人偶、写满生辰八字的黄纸,以及一本手抄《弥勒降世谶》。更令人震惊的是,被捕之人竟是郭惠妃的贴身老婢??王婆,当年随主入宫,主死后被贬为粗使嬷嬷,隐居净乐堂十余年,竟一直未死!
审讯中,王婆痛哭流涕,直言郭惠妃实为马皇后所害,因妒其得宠,暗施厌胜,致其暴毙。她多年来潜伏宫中,只为复仇。而此次目标直指朱雄英,因其生辰八字与当年夭折的郭子极为相似,她认定此子乃“夺命转世”,必须以邪法镇压,方能让主母安息。
马寻听完供词,冷笑不止:“荒谬绝伦!郭妃之死,太医有案可查,乃心疾突发,与皇后何干?你等妖妇,借旧怨煽动仇恨,实为颠覆朝廷!”
他当即命人将供词呈送朱元璋,并附奏疏一道,力陈三点:其一,白莲教渗透宫廷已久,须彻底清洗内廷女官;其二,净乐堂地处偏僻,监管松弛,建议裁撤或改制;其三,今后皇子教育之地,须由锦衣卫与东宫护卫双重把守,严禁无关人员进出。
朱元璋阅罢,勃然大怒,批曰:“妖婢乱法,斩立决!牵连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革职查办。净乐堂即日封闭,余者迁往灵谷寺奉香。”又特旨嘉奖马寻:“识微见远,护国有功,赐黄金百两,绢五十匹。”
风波再平,然马寻深知,树欲静而风不止。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些执迷不悟的老奴,而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舆论的朝臣。白莲教能十年潜伏,必有内应接应。那名礼部主事不过棋子,真正的黑手,恐怕仍在庙堂之上。
数日后,他借探望常升之名,赴北平一行。常升伤势已愈,正在军营操练士卒。兄弟相见,感慨万千。马寻屏退左右,低声问道:“你在北境遇袭,可还记得那支箭的样式?”
常升皱眉回忆:“箭镞较宽,尾羽染红,像是……像是辽东铁骑所用。”
马寻心头一震。辽东铁骑,隶属燕王朱棣麾下。朱棣虽年幼,然自幼聪慧果决,深得朱元璋喜爱,已显锋芒。若真有人借白莲教之手挑动储君与藩王对立,那幕后之人,极可能是某些意图扶植藩王夺嫡的势力。
“此事暂且按住。”马寻叮嘱,“不可声张,但你要密切留意北境动静,若有异常调动,立即飞鸽传书。”
回京途中,他又接到宋氏佑来信。信中写道:“近日伴读之时,李景隆屡次试探雄英对藩王看法,又言‘天子不必出自嫡长’,似有所指。我佯作不解,敷衍过去,然心中惕然。”
马寻捏着信纸,久久不语。李景隆乃李文忠之子,勋贵之后,素来亲近燕王一系。此人若已开始动摇东宫正统之论,说明朝中裂痕已然显现。
当晚,他独坐书房,提笔修书两封。一封致朱标,劝其加强对伴读子弟的甄别,凡有异言者,即刻遣返;另一封致朱?,嘱其在藩地广布耳目,尤其注意兵权交接与官员任免,切勿轻信他人。
写罢,他推开窗扉,夜风扑面。月光如水,洒在庭院之中,照见宋氏佑仍在月下练剑,剑光如练,呼喝有声。马寻凝视良久,忽觉欣慰。这少年虽出身寒微,却心思缜密,胆识过人,将来或可成为东宫臂膀。
半月后,朱元璋下诏,命诸皇子轮流巡边制度正式施行。首站由秦王朱?启程,路线经甘肃、宁夏至榆林,沿途由兵部派员随行记录军情。与此同时,朱标奏请设立“东宫讲读院”,专责皇子教育,由马寻总领其事,章集庆、叶景年等人为讲师,徐增寿、李景隆等人退出伴读名单。
朝野震动,皆知太子势力日益稳固。而马寻之名,亦渐渐传遍南北,被誉为“大明第一国舅”。
然就在此时,边关急报再至:蒙古鞑靼部首领也速迭儿集结五万骑兵,进逼大同,扬言“复辟元室”。朱元璋震怒,召集群臣议战。
马寻列席军机处,力主由蓝玉挂帅,同时建议调燕王朱棣协同防御,既可历练其才,又能观察其行。朱元璋沉吟良久,终允所请。
临行前,马寻单独面见朱棣。少年藩王昂然挺立,目光如炬。马寻淡淡道:“殿下此去,非为建功,而是为证忠。记住,功高震主者危,位卑权重者险。唯有谨守臣节,方能长久。”
朱棣躬身受教:“舅父教诲,儿臣铭记。”
马寻望着这个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皇孙,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未来的风暴不会停歇,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在这洪流之中,为朱标父子撑起一片安宁的港湾。
夜深人静,他再次提笔,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国泰民安,然内忧未除,外患将至。吾辈当如砥柱中流,不避艰险,不负所托。愿我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永续辉煌。”
搁笔之际,东方已泛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