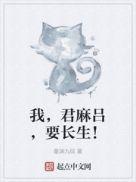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第一国舅 > 第679章 塞王(第2页)
第679章 塞王(第2页)
朱?听着,心头震动。这孩子不过十岁,竟能说出如此言语。他想起自己昨日还在愤恨为何不选他,此刻却羞愧难当。
当日下午,众人亲赴北库。推开尘封多年的铁门,霉味扑面而来。数十名文书官举灯翻检,历时两个时辰,终于在角落一只樟木箱中寻得那份副册。果然记载清晰:该支确系合法出嗣,原判有误。
朱雄英当即便拟奏本,请复其爵,并追赠其父为奉国将军,赐田二十顷,子孙归籍。朱?站在一旁,看着那小小身影伏案疾书,笔锋刚劲,字字如刀刻石。
回程路上,马寻与他并肩而行。夕阳西下,宫道拉长两人的影子。马寻忽道:“你知道为何我推荐雄英,而非你?”朱?默然摇头。
“因为你心中有‘我’,而他心中有‘人’。”马寻望着远处宫阙,“你想要的是权力带来的荣耀,而他想要的是不让任何人蒙冤。前者易堕,后者难欺。”
朱?低声问:“那我……还有机会吗?”
马寻停下脚步,认真看他:“有。只要你愿意放下私欲,从最微末处做起。比如??明日有一桩小事:蜀王朱椿之子周岁,需录入玉牒。你可愿亲手登记?”
朱?一怔,随即郑重点头:“愿。”
三日后,朱?再次踏入玉牒库。这一次,他不再颤抖。他洗净双手,焚香净案,提笔蘸墨,在“蜀王世子”一栏工整写下新生儿的名字、生辰、母氏、封号预拟等信息。每一笔都缓慢而专注,仿佛在雕刻命运。
写毕,他合上玉牒,轻轻吹去墨迹,低声念道:“朱悦?,洪武二十一年九月初七寅时生,母吴氏,嫡长子。”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录入,而是一份生命的确认,一个家族的延续,一种责任的传承。
数日后,朱元璋召诸皇子入殿,论及边防军务。朱棣力主北征扩土,言辞激昂;朱桢则建议屯田固边,稳守为上。争论激烈之际,朱?忽然开口:“父皇,儿以为,治国如修谱??根基不稳,枝叶难茂。与其争疆拓土,不如先清吏治,正宗法,使百姓安居,宗室有序。”
满殿寂静。朱元璋眯眼看他:“你这话,可是从玉牒库里悟出来的?”
朱?跪地叩首:“儿近日随马寻舅父整理旧档,见无数因一字之差而家破人亡者,心甚悲之。故以为,治大国若烹小鲜,须慎之又慎。”
朱元璋沉默良久,忽而点头:“好。你既有此悟,便不必急于封藩。留京三年,协理宗正院事务,由马寻带教你。”
退朝后,朱?独自登上宫城角楼。春风拂面,万瓦如鳞,紫禁城尽收眼底。他望着远处玉牒库的方向,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邓氏送来新裁的春袍,笑道:“七爷如今气色好了许多。”朱?接过衣服,忽然问道:“你说,我将来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值得被人记住的名字?”
邓氏一愣,随即温柔道:“您已经是个好王爷了,这就够了。”
朱?摇头:“不,我要做的,不止是‘好’。我要让后人翻开玉牒时,看到‘吴王朱?’三个字,知道他曾守护过无数人的名字,哪怕无人知晓。”
夜深人静,玉牒库中烛火未熄。朱?独坐案前,翻阅一本旧档,记录着洪武初年一位早夭郡王的事迹。他在页尾空白处轻轻添上一行小字:“此王虽早逝,然其名永载宗谱,不失为朱氏一脉。后之览者,当知姓名之重,胜于金玉。”
合上书册,他起身推窗。月光如水,洒在排排漆柜之上,映出斑驳光影。他仿佛看见无数先祖的目光穿越时空,静静注视着他。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但他已不再迷茫。
从此以后,他不再是那个只想争权夺利的吴王,而是玉牒的守护者,血脉的守夜人。
而这一切,始于一次失败的争夺,一场深夜的悔悟,一杯冷酒,一句教诲,和一页被泪水晕开的“悔过”。
他转身吹灭烛火,轻声说道:“舅舅,我懂了。”
门外,不知何时站着马寻。他听着屋内的低语,微微一笑,悄然离去。
春风拂过宫墙,带来新柳的气息。新的一天,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