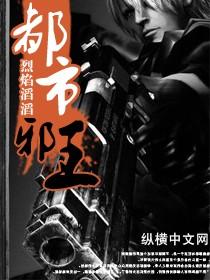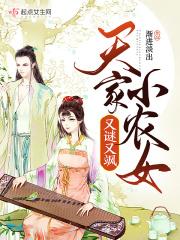笔趣阁>众仙俯首 > 第452章 高手果然是高手(第3页)
第452章 高手果然是高手(第3页)
一位红衣青年踏月而来,足不沾尘,每一步都在空中留下淡淡的音痕。他手中无琴,却有金光流转,如丝如缕,缠绕指间。他站在启言院上空,低头望她,嘴角微扬。
“不是我来了。”他说,声音如风过竹林,“是我终于被听见了。”
沈知意踉跄上前:“你……真的是‘代述者’?”
“我是林砚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他微笑,“他说:‘若天下无真言,我愿化声而行。’于是,我便成了这句话的化身,藏于九渊,等一个能听懂的人。”
他抬手,金光洒落,化作无数细小的文字,飘向全院弟子。每人额前皆浮现出一枚“言印”,形如开口之口,内藏一滴血光。
“从今往后,你们不再需要陶埙。”他说,“你们本身就是言语的容器。说吧,哪怕声音微弱,哪怕无人回应。因为只要有人说,天就还没黑。”
他转身欲去。
“等等!”沈知意伸手,“那你呢?你完成了使命,是不是就要消失了?”
他回头,目光温柔:“或许吧。但言语不死,我只是换一种方式活着??在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里,在你们写的每一个字中。当你想起我时,我就会出现。”
话音落,身影渐淡,最终化作一缕金风,卷起地上一片碎陶,吹向北方。
数日后,帝都剧变。
钦天监监正暴毙,死前在龟甲上刻下最后一卦:“言起于野,天命难掩。”微声堂主果然叛出朝廷,携密档投奔边陲义军,揭露三十年来朝廷如何篡改史书、抹杀异语。北方孩童失语症不治而愈,醒来第一句话竟是:“我梦见一个穿红衣的人,教我说话。”
而启言院,已不再是一座院落。
它成了“言之源”。各地自发建起“听语亭”,百姓将心事刻于石、写于布、唱于歌,投入亭中火炉,火焰燃烧时,竟能传出相似命运者的回应。聋者开始“看”到声音的颜色,盲者“听”到文字的形状。言语,真正活了。
春分后第七日,沈知意再次伏案。
她写下《影语》终章:
>“世人皆以为,沉默是金。
>可他们忘了,金也会锈,也会被埋。
>而言语,哪怕破碎,哪怕被禁,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说,
>它就会找到路,找到耳朵,找到心。
>所以,请继续说吧。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
>无论有没有人听??
>因为总有一天,
>你的声音,会成为别人的光。”
写罢,她放下笔,抬头望天。
万里晴空,无云无风。
但她知道,风一直在吹,只是常人听不见。
而在某座荒村的破庙里,一个拾荒老妪捡到一片紫色碎陶。她不懂字,却莫名哼出一段旋律。隔壁病榻上的孙儿忽然睁开眼,虚弱地笑了:“奶奶,我听见春天了。”
与此同时,九渊深处,万言钟静静悬挂。
钟体新增一道铭文,笔迹清秀,带着几分稚气,像是孩子所书:
>“我也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