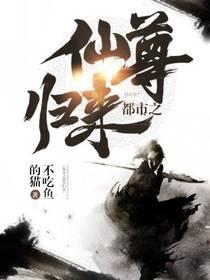笔趣阁>大秦镇天司 > 第868章 三眼青目魔赵洲天剑峡(第2页)
第868章 三眼青目魔赵洲天剑峡(第2页)
她连夜修书三封:一封送往北疆旧部,请他们暗中护送鸣心会传人;一封寄给太史局老学士,请他重审《镇天司源流考》遗漏篇章;第三封,则直呈太子府,标题仅八字:“**言路既开,岂容倒行?**”
与此同时,她在苍梧岭设立“回声堂”,不分年龄、身份、是否失语,凡愿学发声者皆可入门。她不再亲自教授复杂音律,而是让每个学生写下自己最想说却从未敢说的话,再将其谱成简单旋律,由众人齐声吟唱。
第一日,有人写下:“父亲打我,我不敢哭。”
第二日,有人写:“我喜欢同窗的女孩,可村里说女子不该动情。”
第三日,一位老农颤巍巍递上纸条:“我种了三十年田,从没听过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
苏篱将这些话语一一收下,编成《庶民谣》,命弟子们每日黄昏在观言台遗址前奏响。起初只有寥寥数人聆听,渐渐地,附近村民开始驻足,有人低头抹泪,有人跟着哼唱,甚至有个曾参与镇压旧乐坊的老卒,听完后跪地痛哭,自称“听到了良心的声音”。
一个月后,长安街头忽然出现一群流浪孩童,手持竹哨,身穿素衣,列队穿行市井。他们不乞讨,不喧哗,只是轮流吹奏一段五音短调??正是《庶民谣》的主旋律。每当有人问起,他们便递出一张小笺,上书:“此音出自苍梧岭,你说的话,值得被听见。”
舆论骤起。
民间议论纷纷,有赞其唤醒良知者,亦有斥其煽动不满者。朝中大臣分裂两派:一派主张顺应民心,扩大鸣心会办学;另一派则称“音乱则政危”,请求恢复部分监察制度,以防“妖言惑众”。
太子久未表态。
直到某夜,宫中忽闻异响??御花园内的青铜编钟无故自鸣,连响九次,声震四野。守钟人查验并无外力触动,且每次震动,钟体表面竟浮现淡淡墨迹,拼出一行字:
**“若惧真言,何建钟楼?”**
此事震惊朝野。
次日清晨,太子亲赴苍梧岭,未带仪仗,只着素袍,步行登山。他在观言台废墟前伫立良久,最终向苏篱深深一揖:“寡人迟悟,致令忠良蒙冤,民意受抑。今愿重启言政之议,广纳四方之声。”
苏篱扶他起身,摇头不语,只取出一支陶笛,递予太子。
太子接过,迟疑片刻,试着吹了一下。声音干涩刺耳,引来周围弟子轻笑。但他没有放下,反而再次深吸一口气,用力吹出第二个音。
这一次,稳了些。
苏篱笑了。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君王的学习,而是一种象征的转移??权力不再靠压制声音维系,而是学会倾听,并敢于承受那声音带来的震动。
数月后,朝廷颁布新政:
一、废除“清音卫”,严禁任何形式的思想审查;
二、在全国各县设立“鸣心亭”,供百姓自由陈情、奏乐、演说;
三、将《庶民谣》定为民间启蒙必修课,鼓励学校开设“表达与倾听”课程;
四、开放前镇天司档案,允许百姓查阅祖先受审记录,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阿禾的足迹已遍及河西走廊。她在废弃驿站建起简易学堂,用陶笛教牧童识字,用鼓点帮妇人记账,用歌声记录干旱年景下的哀愁。她的身影出现在沙漠边缘、绿洲村落、商旅驼队之间,所到之处,总有人悄悄摘下蒙面的黑巾,第一次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次夜宿沙洲,狂风突至,黄沙蔽月。众人躲入岩穴,恐惧不安。阿禾取出陶笛,在风暴间隙中吹起那段五音短调。起初无人应和,渐渐地,一个孩子跟着哼了起来,接着是一位老妪,然后是整个避难的人群。他们的声音混杂在风吼之中,微弱却执着,如同沙粒下挣扎萌发的草芽。
那一夜过后,当地人称她为“风语者”。
而在长安,苏篱的生活却愈发简朴。她搬离了官赐宅邸,回到苍梧岭一间茅屋居住,每日与弟子们劈柴汲水,耕读吹笛。有人不解,问她为何放弃荣华。
她只答一句:“真正的自由,不在殿堂之上,而在一个人敢不敢在黑夜中说出‘我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