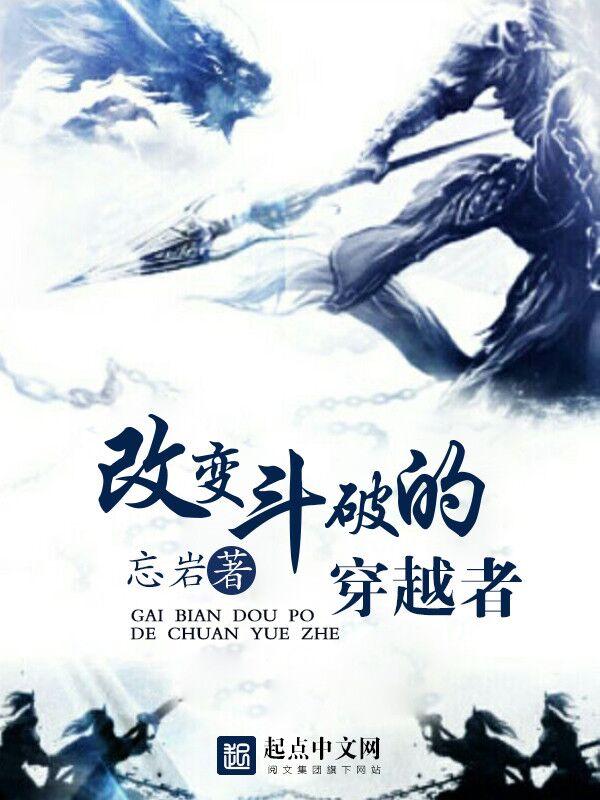笔趣阁>府上有位表小姐(快穿) > 294第 294 章(第1页)
294第 294 章(第1页)
夜色如墨,沉沉压在长安城头。宫灯次第亮起,映得朱雀大街如同一条流动的星河。阿阮与裴砚并肩策马入城,风尘仆仆,却无人上前迎接??皇帝已下旨,此次归京不得举行迎谒仪式,以免扰民。
“他倒学会低调了。”裴砚轻笑,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后的松弛。
阿阮没有接话,只是抬手抚了抚鬓边散落的一缕发丝。她指尖冰凉,掌心却滚烫,那是连日施针、焚药、记录疫案留下的印记。她的袖中还藏着一张纸条,是甘州最后一例痊愈病人悄悄塞给她的:“大夫,我梦见你站在太阳底下,身后全是光。”
这句话,她没告诉任何人。
回到府中,陈嫂早已备好热水与药浴。柳儿捧来干净衣裳时,低声说:“林家老宅那边……今日来了人。”
阿阮动作一顿。
“谁?”裴砚敏锐察觉,转头问。
“说是林婉儿的远房表亲,姓周,从岭南过来的。已在偏厅等了两个时辰,不肯走,只说有要紧事要交给‘阿阮姑娘’。”
林婉儿?那个五年前死于瘟疫、被权贵灭口、尸骨无存的女子?
阿阮缓缓闭上眼,呼吸微滞。这个名字像一根埋在血肉深处的刺,每逢风雨便隐隐作痛。她曾亲眼看着林婉儿被人用麻袋拖走,第二天官府报称“病亡”,连棺材都是空的。可正是这个女人,在太医院藏书阁留下半部《女医札记》,扉页写着:“若后人见此书,请替我活下去。”
她换好素色襦裙,一步步走向偏厅。
那人是个中年妇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衫,脚上一双草鞋沾满泥泞。见阿阮进来,猛地跪下,额头触地,声音颤抖:“阿阮姑娘……我是阿婉临终前托付的人。她在牢里写了三封信,说若有一天有人能走出那条黑巷子,就把信交出去。”
阿阮蹲下身,扶住她肩膀:“你说清楚些。”
妇人从怀中掏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露出三张泛黄的信笺。最上面那封写着:**“致未来执针者”**。
“她让我等十年。我说等不了那么久,她说,‘总会有人来的。只要还有人敢穿白袍进疫区,你就把信交出去。’”
阿阮接过信,指尖微微发抖。
回到房中,她独自燃烛展信。
第一封,字迹清瘦刚劲:
>“当我写下这些字时,我知道自己活不过明日。他们不许女子诊脉,更不许女子揭发疫源真相。可我查到了??那一场‘天降瘟疫’,实为权臣为夺田产,故意放腐尸污染水渠所致。我上报御史台,反被诬陷妖言惑众。
>若你读到这封信,请记住:真正的医者,不只是治病,更是破谎。
>不怕死的人太少,所以我替你先走一步。但你要替我看见春天。”
第二封,墨迹凌乱,似是在极度痛苦中书写:
>“他们给我灌了哑药,舌头快烂了。可我还想说话。我想告诉天下女子:不要怕学不会,不要怕没人信,不要怕孤独。我们不是天生弱,是被当成弱的。
>我这一生,没能救几个人。但我相信,一百年后,会有女子骑马持箱,走遍山川,为人所不敢为之事。
>那时,请替我笑一次。”
第三封,只有短短一行:
>**“阿阮,是你吗?”**
阿阮怔住。
眼泪无声滑落,滴在纸上,洇开一片深痕。
原来林婉儿早知她的名字。早在她踏入太医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在暗处注视着她,期待着她,把她当作火种的承接者。
窗外月光倾泻,照在案头那本《战疫十诫》上,也照在墙上挂着的那一袭白衣??那是林婉儿生前唯一留下画像中的模样:一袭素袍,手持银针,眉目坚毅,如刃出鞘。
次日清晨,阿阮召集群医于府中议事。
裴砚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夜密探回报,当年主导掩盖疫情的那位国公府,近日正在暗中收购药材囤积,尤其大量采购硫磺、雄黄、艾绒,且严禁外泄用途。”
“他们在准备什么?”有人问。
“不是准备防疫。”阿阮冷冷道,“是准备制造另一场‘瘟疫’,再以‘救世主’姿态出现,借此掌控地方医政大权。”
满堂哗然。
“可我们有证据吗?”一位年轻女医怯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