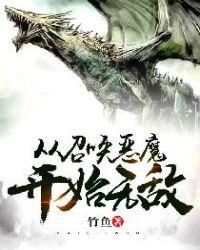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修真界,吐槽出天地异象 > 第四百零六章 瘴气散尽(第3页)
第四百零六章 瘴气散尽(第3页)
不再是为了说服,不再是为了表演,不再是为了赢得同情或掩盖真相。
他们说话,仅仅是因为想说。
阿禾来找他,带来一本手工装订的册子。“这是这段时间收集的故事。”她说,“没人要求交,也没人评比,可大家还是写了,放在村口的木箱里。”
苏小满翻开第一页,是一幅孩童画的画:一个大人蹲在地上,认真听着小孩说话,头顶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妈妈这次没看手机。”
第二页,是一位老兵写的信:
>“我对不起那个被我误伤的少年。我不奢求原谅,只希望他的家人知道,我每个月都在给他坟前放一朵野菊。”
第三页,是匿名的忏悔:
>“我曾经在网络上造谣中伤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让她差点自杀。现在我把这事写出来,不是求宽恕,是怕自己忘了罪孽有多重。”
苏小满一页页翻看,眼眶渐热。
他知道,这不是胜利,而是起点。
真正的变革,从不需要宣告。
就像春天不会敲锣打鼓地到来,它只是某一天,你推开窗,发现冰裂了,草绿了,风里有了暖意。
一个月后,许知意宣布关闭“倾听使者”组织。
“我们完成了使命。”她在大会上说,“不是因为我们成功了,而是因为这项工作本就不该由‘组织’来完成。倾听不是职业,是人性。”
台下寂静无声,随后响起稀疏掌声,渐渐汇聚成潮。
林七则将毕生研究整理成《语言觉醒史》,封笔之际写道:
>“语言最初是工具,后来成了武器,再后来成了装饰品。而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学习让它回归本质??作为灵魂的呼吸。”
而苏小满,回到了最初的教室。
他不再讲课,只是每天坐在角落,听孩子们说话。有的讲梦,有的抱怨作业,有的悄悄表白同桌。他从不打断,从不评价,最多点点头,或轻轻回应一句:“嗯,我听见了。”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跑过来问他:“老师,为什么你现在都不讲故事了?”
他笑了笑:“因为你们的故事,比我讲的好听多了。”
女孩歪着头想了想,忽然说:“那你是不是也孤单过?”
苏小满怔住。
片刻后,他点点头:“很孤单。很久以前,我说了很多话,可没人听。后来我就以为,说话是没有用的。”
“那现在呢?”女孩追问。
“现在我知道了。”他望着窗外飘过的云,“即使只有一个人听见,那句话就有了意义。”
女孩蹦跳着跑开,嘴里哼起歌来。
那天傍晚,夕阳如常洒落沙滩。苏小满走出校门,远远看见许知意站在礁石上等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不是密信,也不是公文,而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像是被反复折叠又展开。
“你看。”她递过来。
信是流浪汉写的,字迹歪斜,墨水晕染:
>“我戒酒了。昨天我去老婆坟前说了好久的话,回来时天都黑了。路上遇到个迷路的小孩,我把他送回家。他妈妈请我吃饭,我没敢进屋,就在门口吃了碗面。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原谅我,但我想试试做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