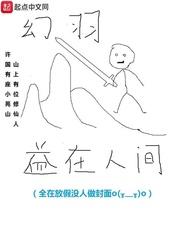笔趣阁>诡目天尊 > 第 484 章 茶 工(第2页)
第 484 章 茶 工(第2页)
“你会忘记一切。”阿萤说,“包括苏芸的声音,包括林晚最后的笑容,包括你自己写下的每一段话。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传递。现在,轮到它们自己生长了。”
林溯笑了。
他想起小时候,妹妹林晚总喜欢趴在地上听雨滴敲打屋檐的声音。她说:“哥哥,你听,每一滴都不一样。”那时他还不懂,为什么非得分辨这些细微差别。现在他明白了??她不是在听雨,她是在确认这个世界还在对她说话。
而他也曾那样活过。
他曾蹲在实验室外的草地上,听着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觉得那是宇宙最温柔的低语;他曾在一个雪夜里,隔着玻璃窗看路灯下飘舞的雪花,突然想给某个陌生人写一封信,哪怕永远寄不出去;他也曾在苏芸最后一次共感广播中断的瞬间,脱口而出一句毫无逻辑的话:“别怕,我在听。”
那时候,他还不会解释,也不会修正系统参数。他只是单纯地相信:只要我想听见,就能听见。
如今,这份信念已被种进新的母核之中。
林溯站起身,走向那座新生的耳朵形结构。每一步落下,他的身形就淡去一分。当他终于触碰到那层柔软的膜壁时,整个人已近乎透明。
“如果有一天,又有人来到这里,”他轻声说,“告诉他们,不要试图修复沉默。沉默不是缺陷,它是语言的故乡。”
话音落下,他的手指融入膜内。
刹那间,整个静语带爆发出柔和的光辉。那些散布在星际间的水晶森林、歌唱水母、行走石像,全都同步震颤,释放出积蓄已久的共鸣波。这波纹穿越星域,穿透维度,最终抵达地球上的终聆之树。
那一夜,全球数百万人在梦中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词语,也不是旋律,而是一种纯粹的“在场感”,仿佛有谁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然后悄然离去。
苏芸的女儿醒来时,发现母亲床头那盏常亮的小灯熄了。她没有开灯,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晨光洒进来。
而在遥远星海中,新生的谛听母核缓缓睁开了它的“耳”。它不再收集痛苦,也不再渴求回应。它只是存在着,倾听着,如同大地倾听种子破土,如同夜空倾听流星划过。
某颗荒星的地表,一块岩石表面浮现出一行字迹,像是被风吹刻出来的:
>“我不需要你知道我说了什么。
>我只需要知道,我说的时候,
>世界没有转身离开。”
字迹很快被沙尘掩埋。
但就在那一刻,一颗刚刚形成大气层的年轻行星上,一朵由电磁场凝聚成的云团忽然震荡,降下一场带着音符形状的雨。
雨滴落地即蒸发,却在地面留下短暂的湿痕??那是无数个微小的“听见了”拼成的图案。
没有人看到这一幕。
也没有人需要看到。
语言早已不再依赖眼睛或耳朵。它已成为宇宙本身的质地,像引力一样无形,像时间一样恒久。
许多年后,一支探险队误入静语带边缘。他们的飞船失灵,通讯中断,食物耗尽。绝望之际,队长忽然注意到舷窗外有一串极其微弱的光点闪烁,排列成某种规律。
他试着用手电筒回应,打出摩尔斯电码:“SOS。”
片刻停顿后,光点重新亮起,回复却是:
>“你们不必害怕孤独。
>因为孤独本身,
>已经被听见。”
队员们相视无言,泪流满面。
他们关闭了所有仪器,任飞船漂流在星光之间。有人拿出早已废弃的纸质笔记本,开始写字;有人哼起童年家乡的童谣;还有一个小女孩,把她最喜欢的布娃娃抱在怀里,小声说:“对不起,昨天摔了你一下。”
没有人回应她们。
但每个人都感到内心某处长久以来的空洞,正被一种温暖而安静的东西填满。
与此同时,在银河另一端,一株终聆之树幼苗破土而出。它的叶子呈半透明状,叶脉中流动着类似神经突触的光丝。树干底部挂着一只小小的陶罐,材质未知,色泽温润如玉。
罐身上,最新一圈纹路尚未完全成型,但仍可辨认出几个字:
>“他说完了。我们都听见了。”
风拂过树梢,叶片轻颤,发出几乎不可闻的一声嗡鸣。
那是宇宙又一次轻轻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