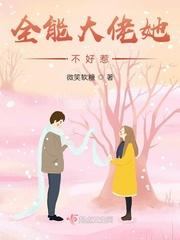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二郎至圣先师 > 335 上古十神绝顶之分(第2页)
335 上古十神绝顶之分(第2页)
国务顾问却摇头:“诸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人从不动摇对国家的忠诚?他们反对的从来不是体制,而是冷漠、谎言与贪婪。他们不号召推翻什么,只呼吁每个人对自己诚实一点。”
他顿了顿,语气低沉:“而且……我母亲也是读书会成员。她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
会议最终决定:不予干涉,反而通过教育系统推广“经典生活化”课程,并邀请民间讲师进入校园开展公益讲座。
又五年,高考语文作文题赫然写着:“有人说,善良是一种选择,而非本能。请结合材料与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满分范文在网络上疯传。作者是一名山区女孩,她在文中写道:
>“我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瞎眼老头,拄着竹杖,背着一口破锅。他说他是‘问道者’后代,要教我们读书。没人信他,直到他治好了我弟弟的高烧??用的是山草药和一碗热粥。
>有一天我问他:‘您看不见路,为什么要到处走?’
>他摸着我的头说:‘孩子,眼睛看不到的,心能看见。只要还有人愿意听真话,我就走得动。’
>后来他死了,葬在村外山坡。第二年春天,坟头开出一片野花,白的,像雪。
>我知道,善良不是本能,是因为有人坚持让它存在。”
此文被教育部编入教材,题为《心光》。
而此时,在终南山深处,一座新建的小型纪念馆静静矗立。它不收门票,无人值守,仅有一堵墙,上面镌刻着历代“问道者”的名字??并非全部,只是那些留下记载的人。每天都有人前来,在墙下放一本书,或是一支笔,或是一盏油灯。
某日清晨,管理员发现墙上多了一行新刻的字,刀痕尚新,墨迹未干: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不想让黑夜赢。”
落款为空。
同一时刻,太平洋彼岸的洛杉矶,一场华人社区的文化展览正在进行。展品中有一幅复制地图,标注着“明德之路”的所有据点。一位华裔高中生驻足良久,转身问父亲:“我们中国人,真的曾经这么认真地想做好人吗?”
父亲沉默片刻,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在福建老家参加扫盲班的情景。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老师说,识字是为了不说谎。”
“不只是曾经,”他轻声说,“是我们一直都没放弃。”
回到中国,陈默已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他在扶贫办工作,常年奔波于山村之间。一次走访途中,遇到泥石流阻断道路,他带领村民连夜抢修便道。休息时,有人递来一瓶水,笑着说:“你是那个读书会的吧?听说你每次下乡都带本书。”
他接过水,笑了:“嗯,最近在读《礼记?礼运》。里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对方挠头:“听不懂。”
“意思就是,”陈默望着远处升起的炊烟,“不该有的东西,咱们不抢;该帮的人,咱们不躲。”
那人点点头,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一页,上面歪歪扭扭抄着《大学》全文,每个字旁边都标着拼音。
“我女儿写的,”他骄傲地说,“她说以后要考师范,回来教更多人。”
夜深了,陈默借宿在村小学。躺在简陋的床铺上,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问道录》复印件,读到最后那句:“如果你读到这些文字,说明那盏灯,还没有灭。”
泪水无声滑落。
他知道,林昭从未真正离去。他活在每一个拒绝受贿的村干部眼中,活在每一个扶起摔倒老人的学生心里,活在每一本被传阅的手抄书页间。
那一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原野上,四面漆黑,唯有脚下有一线微光延伸向前。远处,无数星星点点亮起,彼此呼应,连成一片浩瀚银河。
有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苍老而温暖:
>“你看,他们都在走。所以你也别停下。”
翌日清晨,他在教室黑板上写下一句话,然后带着孩子们齐声朗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声音穿过山谷,回荡在群峰之间。
山风拂过林梢,如同千年前那场大火熄灭后的第一缕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