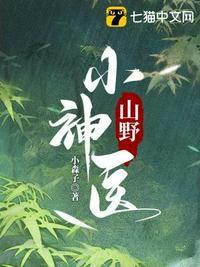笔趣阁>这顶流醉酒发癫,内娱都笑喷了! > 第165章 糊咖答应了全网爆火(第1页)
第165章 糊咖答应了全网爆火(第1页)
于是,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芒果卫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想要通过刚子他们邀请吕铭来参加下一期的《亚洲天王》节目。
面对着芒果卫视这个国内第一地方电视台的求助,刚子和胡涛两个人实在是没办法拒绝。
。。。
夜色如墨,洒落在云南大理的洱海边。湖面平静得像一面未打磨的铜镜,倒映着稀疏的星子与远处村落零星的灯火。陆钏坐在湖畔一块青石上,脚边放着那支鹰骨笛,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笛身上的裂纹??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也是传承的伤疤。
热芭披着一件厚呢大衣走来,手里端着两杯热茶。“还在想今天的事?”她轻声问,将一杯递给他。
陆钏接过,没喝,只是看着袅袅升腾的白气。“沈砚判了七年。”他说,“不是因为打压艺术家,而是‘利用信息权力扰乱公共认知秩序’。法院用了这个说法。”
热芭坐下,靠着他的肩。“你觉得轻了吗?”
他沉默良久,摇头:“我不知道。看到判决书那一刻,我脑子里响的不是欢呼,是一段旋律??我爸在录音带里弹错的那个小节。他本来可以重录,但他留下了。他说:‘错误也是真实的组成部分。’”
风掠过湖面,吹乱了她的发丝。远处,周工带领的技术团队正在调试最后一组设备。他们要在洱海环线布设十二个声音采集点,用最原始的麦克风阵列记录自然之声:雨滴敲叶、蛙鸣起伏、渔船划破晨雾的桨声……这些声音将被编码进《春江花月夜》的新版本,成为“活体母带”的一部分。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在制造另一种神话?”热芭忽然问,“把一首曲子捧成圣物,让它背负太多意义。”
陆钏转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眼睛清澈如少年时初见。“可它从来就不只是一首曲子。”他说,“它是千万人心里不敢说出口的话,是那些被删掉的留言、被屏蔽的直播、被嘲笑的坚持。我们没创造它,我们只是让它重新呼吸。”
话音刚落,手机震动了一下。苏黎发来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函了。他们愿意支持‘千江计划’??以《春江花月夜》为原型,建立全球民间音乐数字档案库。第一批合作国家有十九个。”**
陆钏盯着屏幕,指尖微微发颤。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任何一首来自边缘的声音,哪怕只被一个人哼唱,都将有机会进入人类共同的记忆系统。不再是资本筛选后的“精品”,而是世界本来的杂音。
“你还记得吕铭最后那句话吗?”热芭靠在他肩上,“‘对不起这个国家的耳朵’。”
“我记得。”陆钏低声道,“可我觉得,真正该道歉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太习惯闭嘴了,习惯了笑那些认真的人,习惯了觉得深情就是矫情。我们把自己的耳朵交给了算法,把嘴巴交给了热搜。”
他站起身,走向湖边。水波轻轻舔舐岸边碎石,发出细碎声响。他从包里取出一张U盘,上面贴着标签:**心跳协议?终章**。
这是他和秦澜、苏黎花了三个月时间整理的成果??一份完全去中心化的音频传播协议。它不依赖服务器,不绑定平台,甚至不需要互联网。只要两个设备靠近,就能通过蓝牙或声波自动生成加密通道,自动同步最新版本的《春江花月夜》及其衍生作品。每一个播放者,都是节点;每一次转发,都是备份。
“我们叫它‘心流网络’。”他曾对技术团队说,“不是流量,是心流。当一万个人同时播放同一段旋律,哪怕没有信号,也能形成共振场。”
凌晨三点,第一缕晨雾浮起时,系统启动测试。
十二个采集点同步开启,湖岸响起此起彼伏的鸟鸣虫吟。紧接着,一段钢琴前奏缓缓渗入空气??正是陆明远当年未完成的尾声部分,由AI根据残谱推测补全,但保留了所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感。
琴声与自然交融,仿佛天地本身在演奏。
而在千里之外,成都一位失语症患者正戴着耳机静坐。他是“心跳协议”早期志愿者之一,无法说话,却能感知节奏。此刻,他突然抬起手,在空中轻轻画出一个弧线,像是在指挥看不见的乐团。妻子惊呼着录下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配文只有三个字:**他听见了**。
与此同时,东京某地下Livehouse里,一支朋克乐队突然中断演出。主唱摘下帽子,露出额头上写着“不说谎”的血色字样。“接下来这首歌,”他嘶吼道,“献给所有被当成噪音的真实!”
吉他轰然炸响,竟是《春江花月夜》的重金属改编版,鼓点如战雷,贝斯撕裂虚空。台下观众起初愣住,随即有人开始跟着旋律打拍子,接着是合唱,最后整座建筑都在震动。
同一时刻,非洲肯尼亚一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围坐在一台太阳能收音机旁。老师按下播放键,鹰骨笛的声音穿透电流杂音传来。孩子们睁大眼睛,齐声念出翻译过的歌词:“月亮照着每一条河,就像爱照着每一个孩子。”
而在北极圈内的科考站,中国科研员老陈独自守夜。他打开便携音响,让这首曲子飘荡在极寒空气中。他对镜头笑着说:“这儿连微信都登不上,但我知道,有人正听着同样的声音。这感觉……比团圆饭还暖。”
这一切,都被“心流网络”默默记录。
陆钏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站在洱海边凝望星空时,全球已有超过八万人在同一分钟内播放了这段音频。他们的位置标记在一张隐秘地图上,渐渐连成一片流动的光河,形状竟与长江流域惊人相似。
更令人震撼的是,一些原本被“云镜”系统永久封禁的作品,开始以碎片形式回归??一段藏在老磁带里的女声清唱、一封夹在旧书中的歌词手稿、一段抖音删除后又被用户凭记忆复刻的短视频……它们像散落的拼图,正被无数陌生人自发寻找、修复、上传。
苏黎连夜分析数据,发现了一个诡异现象:每当某个地区出现大规模播放行为,当地主流平台对该曲的相关限流就会失效。不是被破解,而是“规则失效”。仿佛系统自己意识到,压制已毫无意义。
她在内部报告中写下一句结论:**当共鸣足够强大,算法会自我瓦解。**
一周后,央视推出特别纪录片《声音的长征》,全程跟拍陆钏重走父亲三十年前的采风路线。从新疆喀什的老乐坊,到广西侗寨的鼓楼,再到东北赫哲族渔村的雪屋……每一站,都有人拿出珍藏的录音、手抄谱、甚至口传心授的记忆片段。
在内蒙古草原,一位百岁长调艺人听完修复版《春江花月夜》后,颤抖着站起来,用尽力气吼出一段古老呼麦。录制结束后,老人握着陆钏的手说:“你爸来的时候,我说艺术是风。现在我明白了,风不怕墙。”
回到北京那天,陆钏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泛黄,字迹娟秀:
>“我是你父亲的学生林溪。你说我没死,是对的。我只是选择了消失。这些年我在西南山区教孩子唱歌,用最土的办法,一支笔、一块黑板、一把破吉他。我不恨这个世界,我只是不想再被它定义。但昨晚,我听到了那段音频。原来还有人记得‘真诚’两个字。我想回来,不是为了成名,而是想告诉更多人:你可以哭,可以怒,可以跑调,只要你还在唱,你就没输。”
信末附了一张照片:一群山里孩子站在简陋教室前,举着自制的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句话:**老师,我们要唱真话!**
陆钏把信读了三遍,然后拨通苏黎电话:“联系教育部,启动‘种子教师计划’。我们要在全国找一百位像林溪这样的老师,给他们资源,让他们带着孩子们写歌、唱歌、说出心里话。”
“你会被说作秀。”苏黎提醒。
“那就作一次秀吧。”他笑了,“如果能让一百个孩子学会诚实表达,哪怕被人笑话,我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