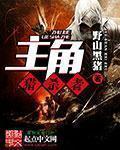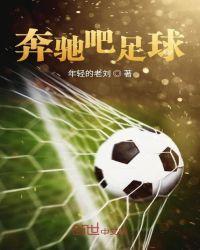笔趣阁>这顶流醉酒发癫,内娱都笑喷了! > 第167章 何老师担忧杜胖子还骄傲上了(第2页)
第167章 何老师担忧杜胖子还骄傲上了(第2页)
抵达目的地后,他见到了当地非遗保护站的负责人阿依古丽。这位维吾尔族女性递给他一卷泛黄的手稿:“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十二木卡姆’残谱,据说是清朝年间一位汉人乐师帮忙整理的。最近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其中一段变奏,和你说的那个‘纳格拉调’几乎一模一样。”
陆钏接过手稿,指尖抚过那些褪色的音符标记。果然,在第七节转折处,出现了熟悉的下行五度滑音,气息标记方式也如出一辙。
“也许从来就没有‘你的音乐’‘我的音乐’。”阿依古丽轻声道,“只有愿意倾听的人,和愿意分享的人。”
当晚,他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举行了一场露天音乐会。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只有篝火与星空。陆钏吹起鹰骨笛,阿依古丽弹起都塔尔,两位从未合奏过的musician,在即兴中找到了惊人的默契。当《春江花月夜》与《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时,现场百余名观众自发跟着哼唱,语言不同,调式各异,却奇异地融为一体。
一位老牧民听完后抹着眼角说:“这声音,像我小时候听爷爷讲的故事,说从前天上掉下来一颗星,落地变成河,河水流到哪里,人们就能听懂彼此的心。”
归途中,陆钏接到苏黎紧急通知:“‘人间低语’装置作品将在联合国总部永久陈列。策展方要求提供一句寄语,不超过二十字。”
他想了许久,最终写下:“**让每个沉默都成为序章。**”
夏季来临前,一件更令人动容的事发生了。那位曾在直播间说出“妈妈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病情”的癌症晚期患者家属联系“千江计划”,带来一个U盘。里面是他母亲临终前三天录制的最后一段话,背景音乐正是她最爱的《春江花月夜》。
“我想告诉你们,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听着这段曲子,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男子哽咽着,“她说:‘原来死亡不是黑暗,是很多人一起唱着歌走。’”
这段录音被命名为《晚安》,加入《人间低语》系列,并在清明节当天于全国三百个社区公共空间同步播放。许多医院病房打开电视,陪护家属戴上耳机,静静聆听。有护士回忆:“那一夜,走廊特别安静,但不像往常那样压抑。更像是……一种温柔的告别。”
秋天的第一场霜降落下时,陆钏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极科考队员的信。信纸边缘结着冰碴,字迹冻得有些模糊:
>“昨天极夜刚开始,我们打开了你留下的极地广播仪。信号稳定,频率清晰。午夜时分,整个基地的人都听见了那阵震动。有人抱着睡袋发呆,有人默默写下一封信塞进时间胶囊。最神奇的是,一只常年不愿接近人类的北极狐,竟然趴在广播器旁蜷缩了一整夜。
>
>我们决定把它命名为‘月照’。
>
>陆老师,你说如果文明真的崩塌了,至少留下一首歌。可我现在觉得,也许这首歌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不需要文字,不需要城市,只要还有心跳,它就不会消失。”
陆钏读完,走到院中。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今年开得格外早,细碎白花随风飘落,像一场无声的雪。
他拿出手机,给所有“千江计划”核心成员群发了一条信息:“准备启动‘种子回声’行动。我们要把这套系统开源,交给普通人。不限地域,不论技术背景,只要你想传递声音,我们就给你工具。”
苏黎回复:“不怕失控吗?”
他答:“真正的秩序,从不是靠控制建立的。是共鸣。”
冬至那天,第一套开源包上线。二十四小时内,下载量突破百万。农民用它改造村头大喇叭播放家书,留学生在异国宿舍组建“跨洋合唱团”,甚至有监狱囚犯请求接入系统,在放风时间集体哼唱《春江花月夜》。
而在新疆吐鲁番的一个小学课堂上,孩子们正跟着老师学习填写新歌词。黑板上写着主题:“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
一个小女孩举手念道:
>“别怕声音小,
>别怕没人听,
>只要你还记得怎么哭,
>就一定能学会怎么唱。”
全班鼓掌。
老师笑着问:“你们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
孩子们七嘴八舌:“是陆钏!”“是他爸爸!”“是所有人一起写的!”
老师点头:“最后一个答案,最接近真相。”
窗外阳光洒进来,照在每一张稚嫩的脸庞上。远处风车缓缓转动,电线嗡嗡作响,仿佛整片大地都在轻轻哼唱。
陆钏此时正坐在工作室,看着实时数据地图。红点遍布城乡山海,每一个都在微微闪烁,如同星辰初升。他打开录音软件,对着麦克风说了句什么,然后点击上传。
几秒钟后,这句话化作一段音符,融入《人间低语》的洪流之中。
没人知道他说了什么。
但一定有人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