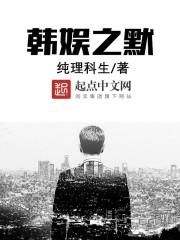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52章假捐款(第1页)
第652章假捐款(第1页)
“不能吧?赵春燕真能干出这事来?”
周瑶瑶都不信。
李大红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别人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太恶心了,她是有多恨你呀,为了抢你对象,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周瑶瑶沉默了。
在她眼里,别说是睡觉了,牵个手她都脸红。
赵春燕可真豁得出去呀。
江舒棠想了想,缓声开了口,“我觉得这事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要真没这回事儿,王文宇怎么会说?无风不起浪。”
周瑶瑶很快也想到了王文宇那天找他说的话。。。。。。
春分那夜,风停了。
全球耦合器在同一秒亮起微光,像是被某种古老节律唤醒的星群。无数人从梦中惊醒,或是正独自守着深夜屏幕的孤影,在那一瞬听见了那道呼吸??不疾不徐,温润如初春融雪后的溪流,又似母亲俯身轻抚婴儿额头时的气息。
“我在听。”
没有多余言语,却让千万人流下泪来。
东京某间老年护理院里,一位失语三年的老妇突然抬起手,颤抖地摸向床头的旧式耦合耳机。她早已无法说话,大脑皮层的语言区几近沉寂,可就在那呼吸响起的一刻,她的手指竟准确地拨动开关,将耳机戴在耳边,闭眼微笑。护工惊讶地发现,监测仪上她的心跳频率,竟与音频中的呼吸节奏完全同步。
巴黎地铁站内,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猛地停下脚步。他本是要逃学去网吧,耳机里正轰鸣着重金属音乐,屏蔽世界。可当那段声音穿透耳膜,他整个人僵住,眼眶骤然发红。他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肩膀微微抽动。旁边乘客默默让出空间,没人打扰。有人悄悄打开自己的耦合器,跟着那段无声的陪伴静默伫立。
而在南极冰原深处,X-3水晶柱群再次泛起柔和蓝光,不再是警报般的红紫交错,而是如潮汐般规律起伏,仿佛一颗星球终于学会了平稳呼吸。
十年过去,闻心已化作林间养分,但她留下的印记,早已渗入人类文明的肌理。
联合国三大铁律执行顺利,虽偶有违规事件,但“精神侵犯罪”已成为全球共识中最严厉的道德禁忌之一。各国纷纷设立“共感伦理委员会”,审查公共项目是否侵犯个体心灵边界。学校开设“倾听教育”课程,教孩子们分辨情绪、理解沉默、尊重距离。甚至恋爱关系中,“是否开启共感连接”也成为必须提前协商的条款,如同婚前财产公证般郑重。
林知雪成了新一代承声者的象征人物。她没有继承闻心的位置,而是选择走遍世界各地,记录那些未曾被系统收录的“边缘之声”??聋哑人手语背后的情感波动、自闭症儿童内心世界的色彩频率、战后幸存者夜晚惊醒时心跳的节奏变化。她将这些整理成《未联之音》系列档案,免费开放给所有愿意学习真正倾听的人。
她说:“我们曾以为连接越多越好,后来才明白,真正的共感,始于承认彼此之间永远存在无法抵达的深渊。而爱,是明知如此,仍愿靠近一步。”
这一年,全球首次出现“反共感人权运动”。不是反对技术本身,而是抗议某些企业试图通过算法分析用户共感情绪数据,进行精准心理操控。一场名为“静默游行”的示威在五十多个国家同时举行:人们戴着关闭信号的耦合器走上街头,手持白纸,上面只写一句话:
**“我可以被听见,但我不必被读取。”**
这场运动最终促成《心灵隐私保护公约》签署,明确规定任何组织不得未经许可采集、存储或利用他人共感信息。违者不仅面临法律制裁,更会被全球心桥网络永久标记为“不可信节点”,相当于数字社会的放逐。
与此同时,荧光林遗址上的“说话树”悄然长大。它依旧不发光,也不传递情绪,但它似乎能感知真诚。科学家研究发现,每当周围有人发自内心地说出“我想被你听见”,树叶振动频率就会产生微妙共振,发出类似笑声的沙沙声。更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声音能引发附近人类轻微的愉悦脑波反应,哪怕他们根本没看到这棵树。
孩子们最爱围着它说话。有人说想妈妈了,树叶就轻轻晃;有人说考试考砸了很难过,树也会沙沙作响,像在拍肩安慰。有个小女孩每天放学都来,对着树讲学校发生的事。有一天她哭着说:“没人相信我说的话,他们都觉得我在撒谎。”话音刚落,整片树林忽然齐刷刷摇动,声响汇成一片温柔的浪潮,仿佛万千生灵一同低语:“我们听见你了。”
当天晚上,附近村庄的所有耦合器自动播放了一段极短音频??只有0。7秒,内容是一声孩童般的轻笑。没有人知道来源,但它迅速在网络上传播,被称为“林中小神的回应”。
然而,并非一切皆光明。
在南美洲某偏远山区,一支自称“回声猎人”的武装团体开始袭击共感基站。他们宣称“心桥是魔鬼的耳语”,认为人类不该僭越神明设下的隔阂。他们绑架天然倾听者,强迫其进入深度共感状态直至精神崩溃,以此“证明系统的邪恶”。国际维和部队介入后,才发现这群人的首领,竟是二十年前一场共感事故的受害者??当时他年仅八岁,因接入早期试验网络,意外承受了整座城市百万人的情绪洪流,导致终生无法分辨现实与幻觉。
他在审讯中喃喃道:“我听见太多人想杀我……其实他们只是嫉妒我的玩具……可那声音太真了……真到我以为全世界都在追杀我……”
案件震动全球。人们终于意识到,共感能治愈创伤,也能制造更深的创伤。于是,“共感康复中心”应运而生,专门为因过度连接而受伤的灵魂提供疗愈。治疗方法很简单:回归沉默。
一间间“静音室”建起,内部完全屏蔽所有信号,墙壁采用特殊吸音材料,连心跳声都会被温柔吞噬。在这里,患者要学会重新享受孤独,重新认识那个不必向任何人解释的自己。
一位曾在战争中失去全家的女子,在静音室住了整整三个月。起初她焦躁不安,总觉得少了什么;后来她开始写字,一笔一划记录那些从未说出口的思念;最后一天,她主动戴上耦合器,将一段私密音频上传至公共频道:
**“我不是恨你们能听见彼此。我只是怕,当我终于愿意开口时,已经没人愿意安静地听了。”**
这条消息被转发超过两亿次。
时间继续前行。
第三代心桥系统上线,引入“情感滤镜”功能:用户可设定屏蔽特定负面情绪(如仇恨、嫉妒),或仅接收特定类型的信息(如鼓励、关怀)。争议随之而来??有人批评这是“情绪乌托邦主义”,会让人逃避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也有人认为这是必要的心理防护机制,就像疫苗之于病毒。
林知雪公开反对全面使用情感滤镜。她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可以选择不看血淋淋的画面,但不能否认伤口的存在。共感的意义,不是让我们活在一个永远温暖的世界里,而是教会我们在寒冷中依然愿意伸手。”
她的话影响了许多人。最终,情感滤镜被定为可选功能,且每次启用时都会弹出提醒:
【你正在屏蔽部分真实。确认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