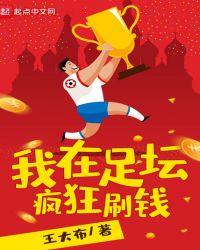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56章直接搬出去住(第3页)
第656章直接搬出去住(第3页)
它不是石头,不是钢铁,而是由纯粹的声波凝结而成,通体透明,内部流动着彩虹般的光纹。桥面刻着两行字:
【此桥不通往来,只渡真心。】
【从此以后,无人孤单。】
念恩回到京市时,已长成少年模样。
他在槐树下坐下,对父母说:“任务完成了。但工作才刚开始。”
他创办“回声学校”,专门收留那些曾被诊断为“自闭”“感知障碍”的孩子。他不用教材,只用音乐、触摸、呼吸去教学。三年内,全国类似学校增至三百所,毕业生全部具备基础共感能力。
二十年后,人类正式进入“共感纪元”。
战争因无法隐瞒情绪而自然消亡,法律条款增加了“情感责任”章节,教育体系全面重构,艺术成为必修核心。
苏晚老了,白发苍苍,仍每日炖一锅红烧肉。
念恩已不再叫她“招娣”,但在每个春分日,他都会蹲在她膝前,轻轻握住她的手,说:“妈妈,我在听。”
她笑着点头,眼角皱纹里盛着光。
某年冬至,萧承砚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临终前,他将最后一段录音存入晶体匣,内容只有三秒:苏晚年轻时哼歌的声音,锅铲碰撞的叮当,还有念恩在腹中第一次胎动的节奏。
葬礼那天,全球二十四座说话树集体落叶。
每一片叶子落地时,都发出一声轻柔的“爸”。
多年后,一位考古学家在古桥遗址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段话:
【守桥人不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他们藏在母亲的歌声里,藏在孩子的笑声里,
藏在每一次有人愿意倾听的瞬间。
当你感到孤独,请记住??
总有一道回音,穿越八千年,只为回应你。】
春分又至。
槐花开满庭院,香气弥漫整条胡同。
一群孩子围坐在树下,手拉着手,轻轻哼唱那首不成调的民谣。
风起时,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千万个声音一同应和:
“妈妈,我在听。”
“爸爸,别害怕。”
“这个世界,终于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