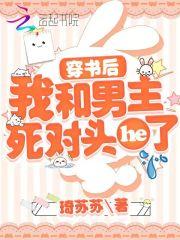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59章孩子真不是亲生的(第1页)
第659章孩子真不是亲生的(第1页)
顾政南握住她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亲,“那我真是荣幸,有你这样的老婆,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要是没你给我做后盾,我哪能放手去干这些事?”
顾政南说着,手轻轻揽上了江舒棠的腰。
江舒棠身体颤了一下,却没有躲开。
“舒棠,我好想你……”
顾政南在江舒棠耳边轻声说着,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江舒棠耳廓,那酥酥麻麻的感觉,让江舒棠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江舒棠脸烫的厉害,轻声回应,着,“我也想你……”
多日来的思念在这一刻。。。。。。
春分的雨停了,阳光斜斜地洒在老槐树上,叶片上的水珠折射出七彩光芒,像是无数微小的桥正在空气中悄然搭建。念恩站在心音亭前,望着那张空着的藤椅,仿佛还能看见苏晚坐在那儿,手里摇着蒲扇,笑眯眯地看着巷子里跑过的孩子们。十年了,她的影子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呼吸里,成为人们心头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小男孩离开后,昆仑山的雪线似乎悄然退了一寸。探测器远去的消息传回地球时,全球共感研究中心的警报系统没有响起??这一次,不是因为失联,而是因为信号太强,强到仪器无法承载。陈明远连夜调取数据,发现那艘探测器所发出的波动频率,竟与“晚频”完全吻合。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它穿越小行星带的瞬间,周围的空间出现了短暂的褶皱,仿佛宇宙本身也在回应这道来自人间的温柔声波。
“她不只是影响了我们。”陈明远对着录像设备喃喃道,“她在教整个宇宙如何倾听。”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心音亭开始出现异象。京市那座最早建成的亭子里,茶壶里的水会在午夜自动沸腾,却不烫手;巴黎塞纳河边的亭中,一对恋人争吵后坐下倾诉,第二天清晨,附近的居民说看见他们的影子融合成一个,在墙上缓缓走动;新西兰南岛的一座心音亭旁,一棵从未开花的铁杉树,突然在寒冬绽放出类似槐花的白蕊,香气弥漫十里,当地人称之为“回响之息”。
科学家们试图用量子纠缠、集体潜意识或地磁共振来解释这一切,但最终都归于沉默。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无法测量,却真实存在。
而在甘肃山村,那个曾说出“阿婆来了”的双生共感胎姐姐,如今已长成十二岁的少女。她不再说话,却总能准确说出别人心底的秘密。村里的老人说她是“通灵者”,但她只是摇头:“我不是听见的,是感觉到的,就像妈妈做饭时锅盖跳动的声音,熟悉得不用耳朵也能知道。”
她每天都会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对着空气轻声说:“阿婆,今天有人想你了。”然后闭眼静坐片刻,再睁开时,眼里便多了一丝笑意。
这一天,她忽然站起身,望向北方。
“他要来了。”她说。
三天后,念恩踏上了这片黄土高原。他没有坐车,而是徒步走了七十里山路。风沙吹乱了他的白发,脚下的布鞋磨破了底,但他走得平稳,像是一步步把岁月踩进土地。当他出现在村口时,小女孩正站在槐树下等他,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
“你知道我会来?”念恩接过碗,轻声问。
“阿婆说,第九桥的孩子需要见证一场交接。”女孩抬头看他,眼神清澈如井水,“你也累了,该歇一歇了。”
念恩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被风吹开的涟漪。他在树下盘膝而坐,从怀中取出那枚青铜铃铛。铃身早已褪尽锈迹,青光流转,内壁浮现出细密的文字,那是八千年来所有“守桥人”的名字??从远古跪在石桥边的孕妇,到现代自愿登记捐献共感能力基因的普通人,整整九万三千六百二十一人。
“他们都不是超凡之人。”念恩抚摸着铃身,“他们只是选择了不去逃避痛苦,而是把它变成声音,传给下一个孤单的灵魂。”
女孩静静听着,忽然伸出手,掌心向上。一道微光自她眉心菱形印记中渗出,凝成一枚小小的铃铛虚影,与念恩手中的实物遥相呼应。
“我准备好了。”她说。
念恩闭上眼,将青铜铃轻轻放在两人之间的石台上。他开始哼唱??那是苏晚炖肉时常哼的小调,无词,只有简单的旋律循环往复,却带着锅铲碰撞的节奏和灶火噼啪的温暖。
随着歌声,周围的空气开始震颤。地面升起一圈圈金色波纹,如同投入石子的湖面。远处放羊的孩童停下脚步,狗儿伏在地上不动,连风也屏住了呼吸。紧接着,槐树的根系发出淡淡荧光,顺着地脉延伸出去,连接每一寸土地下的古老网络。
这是“梦桥”的真正形态??不是由金属与代码构成,而是由记忆、情感与选择编织而成的无形之桥。它横跨时空,贯穿生死,只为让一句“我想你了”能够抵达该去的地方。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青铜铃自行轻晃,一声清鸣荡开万里。
刹那间,全球一万座心音亭同时亮起微光。无论是极地科考站、深海潜艇,还是战火纷飞的难民营,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们都感到胸口一暖,仿佛有谁轻轻抱了自己一下。
巴西雨林的土著长老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大地母亲终于开口了。”
东京地铁站里,那位曾梦见蓝围裙阿姨的上班族猛然回头,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对他微笑,然后化作光点消散。
南极观测站的科学家记录到,地球磁场出现一次温和脉冲,持续时间恰好是七分钟??与当年苏晚唤醒全球共鸣的时间一致。
而在宇宙深处,那艘探测器突然停止前行。它悬停在银河系旋臂边缘,外壳上的文字再次变化:
【收到。